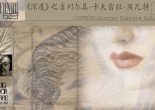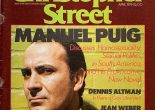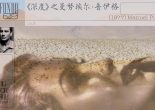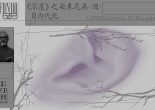掘火B站
微信公众号
掘火电台podcast
掘火旧版
掘火官方微博
作者: anita
自述:
掘火中译:《深度》之阿莱霍·卡彭铁尔
《光明世纪》为我们留下了卡彭铁尔关于革命政治的最坦诚和复杂的思考。书中被赋予了最高智慧的人物不是维克托,不是埃斯特万,而是索菲亚(人如其名)。关于政治行动,我个人确实也想不到比她在小说结尾的选择更好的答案。
03/21/2025 0个评论
马尔克斯和卡彭铁尔谈曼波
马尔克斯和卡彭铁尔为捍卫曼波写下的这些文字,是一份可贵的历史见证。他们愿意为一位正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流行乐手辩护,体现出同那位曼波之王相仿的敢于挑战权威、打破圣象崇拜的自由精神。
01/03/2025 0个评论
掘火中译:《深度》之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
从这种意义上讲,被视为古巴革命的叛徒而于后半生流亡海外、至死再未返回故土的因凡特,反而可以说是抓住了古巴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特征的一位作家。
06/28/2024 0个评论
与曼努埃尔·普伊格的最后一次访谈
访谈发生在1979年,原载于纽约一家同志文学杂志《克里斯托弗大街》(Christopher Street),普伊格在其中谈论了同性恋相关话题和他的第四部小说《蜘蛛女之吻》。那一年,《蜘蛛女之吻》英译本刚刚面世。
12/23/2023 0个评论
掘火中译:《深度》之曼努埃尔·普伊格
和其代表作《蜘蛛女之吻》中的莫利纳一样,他在电影中成长、被电影教化;电影,而非文学,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因为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接触电影之后才开始接触文学的。
12/15/2023 0个评论
《<深度>之博尔赫斯》译者随笔
精彩纷呈的一生。我幻想,能花去几年时间为这样一个人作传,应该是挺幸福的一件事。仿佛是跟他一起活一遍,阅读他喜欢的作品,思考他思考的问题,感受他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06/04/2022 0个评论
掘火中译:《深度》之博尔赫斯
“我多愁善感到令人厌烦。”因此,不同于外界的想象,图书馆及其象征的理性,只是博尔赫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同样在意经验与感受,对勃发于身体层面的野蛮冲动心存向往。
06/03/2022 0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