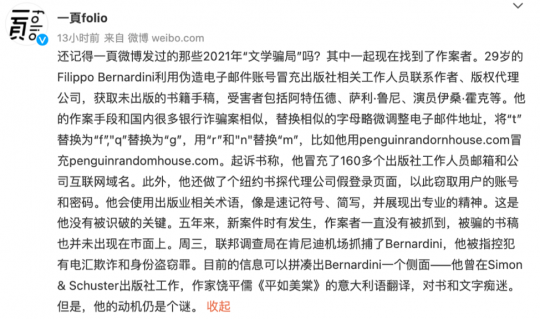《塞维丽娜》(一)
译者序
在掘火刚刚推送的波拉尼奥访谈 (B站)(微信公众号)中,波拉尼奥和主持人谈到盗窃书籍的话题,随后波拉尼奥表达了自己对艺术与犯罪这个搭配的痴迷:“把艺术与犯罪搭配在一起的概念很吸引我。萨德侯爵就曾笔法精湛地讨论过艺术和犯罪。犯罪是门艺术,而有时候,艺术也是场罪行。”危地马拉作家罗德里格·雷耶·罗萨(Rodrigo Rey Rosa, 1958— )发表于2011年的中长篇小说《塞维丽娜》(Severina),讲的就是一个神秘的女偷书贼的故事。跟前面访谈中主持人对波拉尼奥笔下许多人物的形容一样,这位名叫塞维丽娜的美丽偷书贼游走在道德与堕落、理智与疯狂、现实与虚构之间。自本周起,掘火开始连载该小说的中文译本,每周五更新,直至全部完结。
也许部分读者有印象,波拉尼奥在访谈中也提及了雷耶·罗萨,推荐大家去读他的作品,并形容其小说“与任何既有作品都不相像”。雷耶·罗萨的独特叙事风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主要书写对象——危地马拉社会——有着不同于拉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鲜明特征:巨大的贫富差异、复杂的种族构成(玛雅原住民占全国人口近一半)、持续三十年的内战,和战后居高不下的凶杀案发率等等。2012年9月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雷耶·罗萨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留在危地马拉。有时候我觉得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素材了…… 太多事件,乍听就像是虚构出来的。在这类贫富极为悬殊、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人与人之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不必过多构思情节,只需动用记忆,甚至仅仅依靠自动书写就可以完成创作。” 雷耶·罗萨小说中的一些情节直接取自报纸上的新闻,比如《聋儿》(Los sordos, 2012)中对当地报纸所报道凶杀案新闻的罗列,让人想到波拉尼奥《2666》第四部分“罪行”,作者用漫长的篇幅和冷酷的语调陈述发生在墨西哥华雷斯城的奸杀妇女案件。而另外一些故事,虽出自雷耶·罗萨的虚构,他之后却被告知现实中确有其事。比如发表于1999年的《丛林牢狱》(Cárcel de árboles),讲述一帮政客、商人和科学家共同密谋,在热带雨林深处建起一家精神病院,通过在死刑犯身上进行人脑实验来谋取商业利益。作家是在小说面世后的读者反馈中,才得知这并不是虚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有评论者读过《丛林牢狱》之后,说这个故事让他们想到了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和乔治·威尔斯的《莫罗博士岛》。
相较于上述几部描述危地马拉社会现实的代表作,《塞维丽娜》的主题和笔调更为轻松日常。这是一个围绕书籍展开的爱情故事,温情伤感中夹杂着悬疑与黑色幽默,没有宏大的社会视角,而是寄托了更多作家自己的私人情感。与危地马拉裔美国小说家弗朗西斯科·高德曼(Francisco Goldman, 1954— )一次对谈中(Bomb Magazine, 第125期,2013年10月),高德曼问起《塞维丽娜》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雷耶·罗萨解释说,当时他刚结束一段感情,正深陷于失恋情绪,为了躲避空虚和抑郁,他把这股负面能量用于创作,塑造出了塞维丽娜这么一个形象。“就像,让光照进来”(“Like letting the light in”),高德曼这么评论。雷耶·罗萨表示赞同,并补充说这个故事“是送给我那位前任恋人的一条加密信息。”
虽然整部作品充斥着一个痴情者的苦恋和呓语,故事讲述过程中,偶尔也会有折射出危地马拉残酷现实的碎片一闪而过。比如,后面章节中有一处,叙事者“我”来到女主人公所在公寓,按下门铃后,一位穿制服的女服务生过来开门,看起来还只是个小女孩,“然而脸上那副生硬的表情,却让我想起说不定哪天就被征召入伍的农村儿童,他们的神情也会慢慢变成这副丑恶模样。”在危地马拉,哪怕是内战结束之后,未成年人被军队强征入伍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数不清的家庭支离破碎,造成无数个体和社会层面的悲剧。若说危地马拉社会现实构成雷耶·罗萨一切写作的深层背景,那么摩洛哥,或更宽泛意义上的北非,以及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则是另外一些时常出现在他小说中的元素。比如《塞维丽娜》中一个重要人物艾哈迈德,就是一位来自摩洛哥的书商。这是因为在雷耶·罗萨于1996年危地马拉内战结束后回国定居之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摩洛哥。也正是在那里,他与美国作家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 1910—1999)结为好友,后者把雷耶·罗萨介绍入英文世界,并亲自将其最初几部小说翻译成英语出版,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丛林牢狱》。
虽然主题和故事氛围与其他主要作品大相径庭,梦境依然构成了《塞维丽娜》这部小说的重要元素。雷耶·罗萨笔下的世界,往往是现实与梦境交错,人物行动的动机常常是基于非理性的想象,比如被恐惧催生出的妄想,或者似醒似梦中看见的景象。1994年发表的《塞巴斯蒂安的梦》(Lo que soñó Sebastiá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故事从头到尾都没有澄清,主人公在那天深夜究竟是梦见了一场枪击,还是他事实上被设计亲身参与了对邻居的谋杀。雷耶·罗萨热衷于诉诸梦境和迷幻,来扰乱人物对现实世界的习惯感知。这一风格当然是有来自作家所身处社会现实的影响:凶杀案频发的暴力日常,恐惧所激发的偏执妄想,再加上外人难以理解的神秘玛雅文明,这些都使得危地马拉作家笔下的世界弥漫着一种诡异不安的氛围。另一方面,从雷耶·罗萨个人的文学趣味角度讲,他这种不断扰乱现实与虚构边界、打破时空边界的奇幻写法,背后的哲思和美学源泉,其实就是他最为推崇的作家,博尔赫斯。在他整个少年时代和成年早期,雷耶·罗萨都在不断重读博尔赫斯,用他自己的话说,博尔赫斯让他同时成为了一个读者和一个写作者。博尔赫斯对他的深刻影响在多部长篇和短篇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塞维丽娜》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博尔赫斯曾说,“如果有天堂,那它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 《塞维丽娜》这个故事背后,也有一个书籍的宇宙若隐若现。男女主角因书而相识,在女主消失的日子,绝望的男主一度想通过研究她所盗窃的书单来破解其身份谜团。博尔赫斯以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甚至作为彩蛋出现在了小说结尾。
塞维丽娜一度无故消失,主人公“我”邀请奥托·布兰科先生,那位常陪伴在塞维丽娜左右、身份同样神秘的男人,去咖啡厅谈天,试图从他口中获知关于塞维丽娜的一些真相。布兰科先生描述他和塞维丽娜,以及许多跟他们一样“为书而生”的人的处境,他这样说道:“我们被指控犯有各种恶习、过失甚至罪行。我们被称作特工、诈骗犯,被误认为是用书本来传递加密信息的间谍;还有人说我们专门收集描述各类犯罪或丑闻现象的出版物、书籍副本,或传播这样或那样的色情信息,诸如此类。但我们自始至终唯一在做的事,就只是以书为生。”准备这篇序言的过程中,偶然刷网页,看到“一頁”官方微博介绍了一起神秘的书籍诈骗案,作案者的行为竟可以应和小说中布兰科先生的描述。不禁再次感叹现实世界与虚构文学之间果然是边界模糊,真假难辨。以下是博文截图:
《塞维丽娜》
著 |罗德里格·雷耶·罗萨(危地马拉)
译 | anita
一
她第一次进来我就注意到了。从那一刻起,我就怀疑她是个小偷,虽然那一天她什么也没偷。
“玩家书店”(La Entretenida)每周一下午都会举办诗歌朗诵会。这家店是不久前我和几个书友一起开的。我们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做,又刚好都厌倦了总要花很高的价钱去购买别人按照他们的喜好挑选出来的书。在落后的省级市镇,我们这样的人常被视作怪人。(在这种地方还会碰上更糟糕的事,但我决定暂且不提。)总之,为了不再为书的事厌烦,我们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
我刚刚结束了一段恋情,对方是个哥伦比亚女人。我一度以为她就是我的人生伴侣。一个既简单又一言难尽的故事。在一些人眼里是纯属浪费时间,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一场美丽的冒险。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书店不大,但尽头处有足够的空间摆放桌椅,供举办活动使用。有时就是单纯的诗歌朗读,有时也会有舞台表演、滑稽剧目排练。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下午,城里刚刚下完一场暴雨,雨水漫进书店所在的小小商贸中心的地下一层。从一个店面走到另一个店面,需要高高踮起脚,踩在用水泥和旧砖块临时搭建起来的过道上。她穿着紧身裤,平底高筒靴,白色棉布衫,一头乌黑的发。样子十分成熟。她没有听完最后几首散文诗朗诵就走了,我自己觉得那几首诗非常好。我知道她会再回来的。
我接连好几个下午都在等她。为什么如此确信她会回来呢?我这样问自己。我也不知道。
终于,在隔周的周一下午,她出现了。朗读会已经开始。一帘幕布将书店和诗歌活动空间隔开,她就站在幕布旁边。这次她穿了件稍显宽大的天蓝色棉布连衣裙,裙摆到膝盖——一双显然是精心养护的、优美圆润的膝盖——银色宽腰带,黑皮凉拖鞋,小小背包上镶着亮片。她待到了最后一刻。结束后去吧台喝饮料,与其他顾客交流,临走前,极其敏捷地,从日本文学译著区抽出两本书塞进了包里。只见她从容地推门走了出去。警报器居然没响,我好奇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没有拦住她。像上次一样,我确信她还会再回来。
过了一会,我走到日文区,在一本账簿上抄下刚刚被窃的两本书的名字,记下日期和时间。然后回到收银机旁站着,想象那个女人带着书去了哪里。
下一次见到她是两三周之后了。看到她进来,我先道了一声下午好,接着问她想找什么书。
“想买几本当礼物送人。”这是我从她口中听到的第一句话。
“可以问送给谁吗?”
“给我男朋友。”她答道。难以从口音辨别出是哪里人。
“啊,那您肯定了解他想读什么了。对了,日文翻译区刚进了几本新书。”
她的眼神一下警觉起来。
“啊。”她说,“我喜欢日本人写的东西。”
“在那一片区。”我指了指书店的尽头。“虽然您已经去过了。”
她没有动。
“可是,我男朋友不怎么喜欢。他觉得太流行了。这里有没有…… 切斯特顿的书?”
我机械地笑了一声。“哈,那个家伙。应该有。”我指了指书店的另一边,“应该在那边,更高的那一排。切,对,切斯特顿。”
我重新回到收银台,做出忙着翻阅书目册的样子,好让她放松警惕。她在书架间来回踱步。我隐约听到了一本书滑入她背包的声音(之后核对得知,那是一册加朗译的《一千零一夜》)。她假装咳了一声,顺势将另外两本书塞进包里。几分钟后,她走到收银台,对我说:
“可惜,没找到合适的。我给他买瓶香水好了。”
“需要的时候再来。”我定定看着她。她穿过门口检测通道,警报器再一次没有响。
我走到遭窃区,记下书名:《一千零一夜》,卷一、卷二、卷三。再标注上时间、日期。我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跟踪她出去。
几天后,店里进来一批新书,其中有一套十六开本的俄语译著集。排版设计细致严谨,烫金字体和版画的使用,让装帧看起来尤为精美。我如获至宝,把这套书放在距离收银台很近的书架上,同时保证其中几本的位置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外。这是为她准备的。
一个周四,我终于决定采取行动。那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那天店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翻着书,我远远监视她。没跟她提新进的那套俄语书。她进来的时候我只简单打了个招呼,假装正忙于审核手里的账目。
我朝她走去,她没有察觉。来到她身后,近到能闻见她的发香。
“这次您把书藏哪了?”我问。她吓了一跳,扭身转向我。
“什么?!” 她叫道。 “您吓我一跳。您在说什么啊?”她看我面露笑容,也笑了起来。
“对不起。”
她一只手捂住胸口。
“真的吓到我了。”
“我也说真的,把书藏在哪了?”
这下她看起来是生气了。一双精心修剪的浓眉,此刻微微簇起。她绕过我身旁,迅速向门口走去。我伸手按下保险门的按钮,她在最后一刻跑了起来,但保险门及时落下,把她挡在了店里面。她停下脚步,奋力推拉铁门。
“你在干嘛!”她转过身看着我,喊道,随后从裤子口袋取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放我出去,不然我叫人了。”
“别紧张。”我一边注视着她,一边把照在她身上的一盏防盗反光镜关掉。我看着眼前这位受困的美女,发现她的魅力让人难以抗拒。“别紧张,别紧张。”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她冲我大喊,指着自己的手机,“再不让我出去,我现在就叫人来!”
我观察着她的胸,她的腰身。今天没有带包。她背向我,开始拨号码。完美的背影。
“喂?我需要帮助!”她对着手机说。
“小姐。我们在地下一层,没有信号。我不会伤害你的。把拿走的书都还给我,你就可以走了。我列了一个单子,上面都是被你拿走的书。之前几次都没阻止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吗?为什么?快放我出去!”她又喊了一句,但这次降低了音量。
“你可能不相信,这里、这里和那里,”我朝天花板胡乱指了三个地方,“都有摄像头。我有证据。”
“真的?”这时我听出了一些轻微的阿根廷或乌拉圭口音,她之前一直隐藏得很好。“看起来并没有啊。”她笑了。“对不起。原谅我好吗?”
“怎么原谅呢?就把书都还给我吧。”
她从腋下取出两本俄语小书,从裤子口袋掏出另外一本。带着一股优雅的骄傲和坦然,大踏步走到书架前,把书放了回去。
“好了。”她理直气壮。
“其它的呢?”
“其它的就算了吧?”她试探地说。
“不能算了。这样吧,就当是我跟你之间的一笔私人账吧。我是有合伙人的你知道吗?”我按了下按钮,打开保险门,暗示她可以走了。
她几乎是跑出去的。我紧跟了几步,在她消失在楼梯上之前,问她叫什么名字。
“安娜!”她喊道。
我告诉自己,她会再回来的。站在所有这些书中间,我突然感到十分孤单。多希望摄像头的事是真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