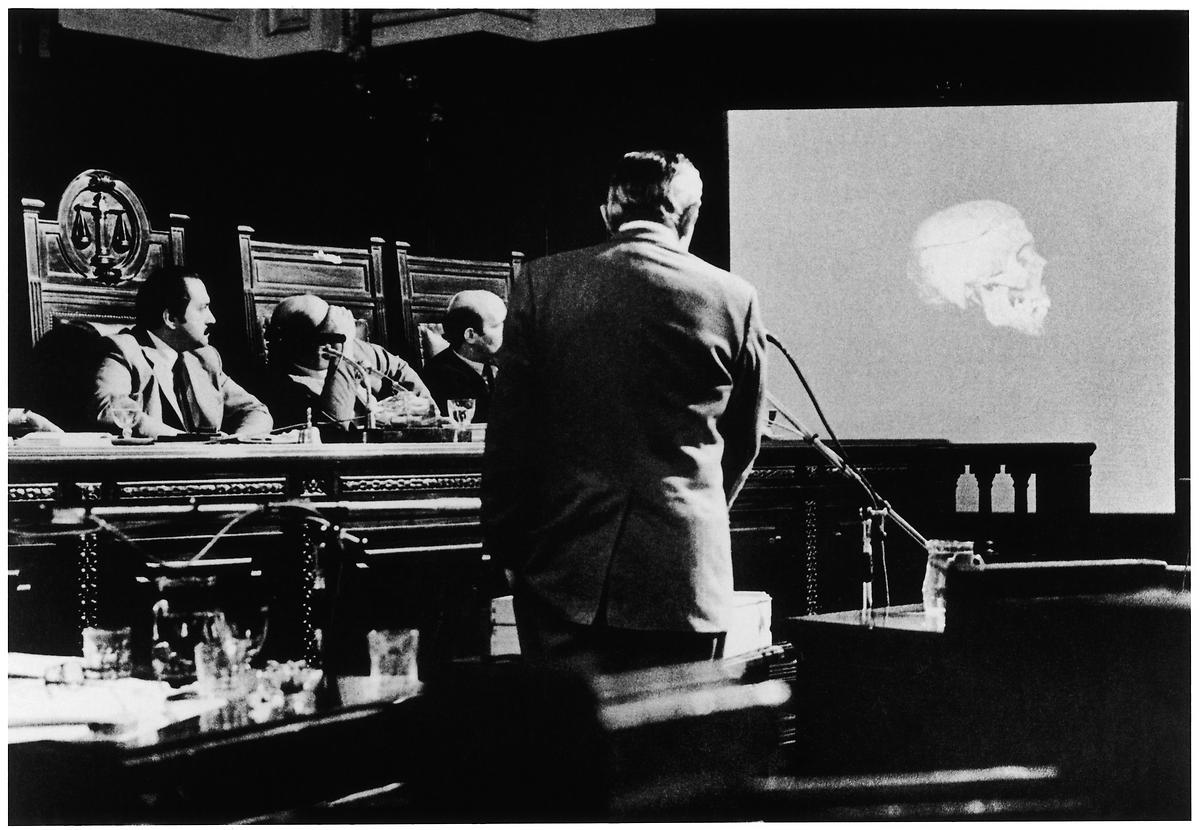如果有一堂關於法庭題材的電影課找我推薦片單的話……
我會堅持的兩部片是第一部與最後一部放的片,分別是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審判》(The Trial,1962)跟橋口亮輔的《周圍的事》(ぐるりのこと。,2008)。
老實說,我並不喜歡看法庭電影,或者跟法律有關的影片,從根本來說,我個人其實非常不相信法律,也許出於主觀,但我認為這可能也是大部分人的看法。所以當我初次接觸到威爾斯的《審判》或甚至因而讀了該片所根據的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同名小說時,我會如此痴迷,因為即使是出自一個法外人的身份來談對「法」的看法,可這卻是一般普羅大眾的情況。影片敘述一位叫「K」的人被告知自己「被捕了」,但不需要拘禁,可是他既不知道犯了什麼罪,也不知道究竟如何擺脫這個訴訟,於是他徒勞地展開行動,但事實上他根本不知道到底該展開什麼樣的行動,直到最後由兩名於故事開始時來告知他被捕消息的人把他處死為止。
如此荒謬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將法的程序與邏輯透過超現實的方式進行嘲諷,進而提供一些思考空間給觀眾。所以我會希望,即便影片內對「法」的觀感可能會讓法學院學生感到幼稚、無病呻吟都好,但我也希望這些專業的法內人,能夠重新去思考一下,他們所認知的「法」跟大眾所知道的「法」有怎樣的差距。所以我首先希望能讓學法的人看到這樣的影片。但,風險是,這部影片畢竟是威爾斯的「壯年電影」,它有難度,甚至對學電影的人來說都不輕鬆了,對這些非電影專業人來說,肯定是挑戰。但,他們將來都要面對比理解一部影片更要難上百倍的案件,這種挑戰我想也是應該面對的。而且影片本身極為突出,這也是無可否認的。
至於《周圍的事》,有意思在於,法庭的段落在影片中沒有任何「主導」的位置,但它(們)卻直接深植於,或者說以某種結晶的方式,將主要人物的一些至關深邃的傷痛給封閉、聚集起來。而這種行為(訴訟)卻又是無時無刻都在我們「周圍」發生,尤其在身為法庭畫家的主人公身邊,如此緊密又如此疏遠,卻又在絲毫沒有任何察覺的情況下,法,已經深深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沒錯,我們當然是生活在被法給包圍、治理的環境中。這部片在安排這樣交錯的構想上,非常值得讚賞,即便偶爾會因為導演的憤世嫉俗而突出某些社會的扭曲性,但,又有何不可?再說,這位日本新生代導演也透過這部片傳達出他深厚的電影功力,對觀眾來說,無疑不是一件好事。當然,學生能從中品嚐多少,這又是另當別論了。影片的主人公雖有美術長才卻在一個小的修鞋攤上工作,直到一位在電視台工作的學長邀他到法庭替電視台繪製法庭畫像賺外快,他才收起鞋攤工作而全心畫畫;與此同時,他那個因懷孕而結婚的老婆雖可得心順手地應付出版社的美編工作,卻仍感到壓抑,兩夫妻之間的壓抑直到小孩出生便夭折後達到頂點。兩人遂於日常、工作、親友之間的大小事件中,慢慢解開彼此的心結。
其他作品我試著將相關的影片聚集在一起,讓它們彼此以「類聚」方式呈現出近似主題或概念的多樣性。
在我所接觸過的法律(庭)影片,許多都跟律師的自省有關,推測是創作者對法也有跟一般人近似的態度,很難說他們是要讚揚法律還是指控它,我相信動機往往以後者為多,即使有時候這些商業片(法庭片似乎在好萊塢被拍攝的機會大大超過其他國家)會礙於「中庸」而使得影片在道德判斷上處於某種曖昧與不明。總之,這類影片除了經常要揭露出法在「程序」上的黑暗之外,也算是變相地要喚起法律從業人員的良知。假如「法外人士」對法律有這麼負面的成見,那麼是不是法內人士需要負起責任?還是抹黑這個「法的世界」的媒體需要負責?這種問題還是丟還給法內人好了。
這類影片中,有一些有名的片,我想應該已經變成「權威片」了吧?像是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1997)。這部影片主要是描述一位年輕剛從學校出來要涉入法律界的法學院學生,如何一開始便因為「正規」的法律事務所一位難求轉而進入了一個稍微不那麼正規與合法的事務所內工作,卻因為一件醫療保險理賠的案件而逐漸發覺了法律程序與體制的腐敗,進而在一些正義感以及情感力量提升的情況下,挺身對抗一個有名的大事務所,其實也等於是在對抗一個體制,這樣的故事。雖然乍看本片是有一個精彩的劇本,但事後想想,裡頭也不乏避重就輕的部分。至於科波拉,算起來應該是做好了改編劇本的工作,而在導演上似乎有點過於服從劇本。但無妨,即使看不到過往他那些深厚但又有點炫耀的手法,至少《造雨人》會是一部紮實的商業片,學生應該不至於反感。唯獨,它因為太有名,很可能已經有大部分的人都看過了吧?
同類型的片,還包括了朱文森(Norman Jewison)的《義勇急先鋒》(…and Justice for All,1979)、盧梅(Sidney Lumet)的《大審判》(The Verdict,1982)、饒立恩(Steve Zailian)的《法網邊緣》(A Civil Action,1998)、哈克福特(Taylor Hackford)的《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1997)、波拉克(Sydney Pollack)的《黑色豪門企業》(The Firm,1993)以及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熱天午後之慾望地帶》(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1997)等等影片,基本上都算得上這種影片,與其說這些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發覺了自己的良心,還不如說這些影片其實是法庭題材的「勵志」片。
說起來法庭片有它先天的優勢,尤其藉由加強「體制」的嚴峻和醜惡,便可以做到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賣錢公式:「壞蛋越大影片越成功」,這也是為何跟法庭(律)有關的影片他也沒少拍。再者,最近為了補課趕了幾部片來看,對於拍攝這類影片的創作者那種「憤世嫉俗」的心得有很深刻的感覺。基於這一點,我覺得這些影片的編劇跟導演,都帶有一種很強烈的憤怒。其中可以以盧梅為代表。
《義勇急先鋒》雖然我看過,但現在除了影片中幾場戲與一些鏡頭之外,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印象,所以關於此片,我直接將DVD盒子上的簡介貼過來:「In a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here criminals go free, lawyers and judges make deals as a matter of routine and the innocent sometimes go unprotected, young lawyer Arthur Kirkland begins to wonder where the justice has gone. Arthur is an honest, idealistic lawyer who is suddenly under pressure to defend a distinguished judge accused of raping and battering a young girl – and whom Arthur knows is guilty. The eccentric, cheerfully suicidal judge who thinks Arthur should play the game. When it comes down to the trial, Arthur must choose between the security of his career and his personal integrity. The final, explosive courtroom scene is unforgettable!」《法網邊緣》的情況也同,這部片應該也已經是10年以上的記憶了,在腦海裡留下的印象更稀薄,DVD殼上的簡介是這樣的:「約翰屈伏塔飾演一位專打人身傷害官司的紅牌律師許立建,他關心的只有自己的財富名聲與地位。為了龐大的和解金,他接下某小鎮水源污染案,居然懷疑孩童罹患血癌和工廠廢水有關,而控告美國兩大企業。進行調查與訴訟的過程中,許立建冒著失去金錢、友誼與事業的危險,爭取客戶的利益……」至於《大審判》則是富有正義感的主人公在墮落了三年後,接到一個委託人、被控者以及他自己都想庭外和解的醫療疏失案件,但在他前往醫院探視那位因醫療疏失而成了植物人的委託人時,他的正義感再度湧來。可是他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律師事務所、宗教醫院、消失的證人、充當間諜的枕邊人、憤怒不諒解他的委託人家屬,當然還有勢利但能力高強的辯方律師。影片光是這樣的設定肯定有張力,可惜在我看來,影片其實一點都不在關照案件,也對答辯過程著墨很少,事實上,還不如說影片是在賣弄兩位明星——保羅‧紐曼(Paul Newman)和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以致於影片中對於很多議題都想涉及,卻都沒有一個深入的,只是盧梅的技巧還是沒話說,觀看過程仍是沒有冷場。
另一類作品,主旨是針對法律結構來的,當然這在前一類作品中也涉及到,不過這些影片關注的重點稍微偏離,比較不那麼統一。朗(Fritz Lang)的《狂怒》(Fury,1936)批判的是「私刑」的問題,他的主人公被冤枉入獄,狂怒的人們甚至來破壞監獄、要以燒毀監獄的方式向主人公行私刑,但主人公卻反而因此逃脫,反過來想向這些人們復仇,但最後卻又在良心發現的情況下自動歸案。朗在美國時期的作品中,不乏涉及這類跟法律相關的議題,不過說起來影片真正跟法的連結是表面而微弱的,因為在訪談中他自己也表示,他真正感興趣的,是人無法逃脫自己的命運這樣的中心思想。他後來還有一部名為《排除合理的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1956)的作品,便是讓主人公製造假證據,讓調查的方向都指向他自己,但最後卻因為他的詭計成功,而讓法官將實際上就是兇手的他判了無罪。這部片可以說非常有趣,值得放給學生看。不過可惜的是本片同樣在審訊的呈現上相對薄弱。
希區柯克的兩部作品《懺情恨》(I Confess,1952)和《伸冤記》(The Wrong Man,1957)則是從兩個面向來探討法律。前者處理一個知道真兇但基於神職人員不能透露告解內容的理念,即使後來證據都指向他自己是殺人犯,他依舊不願意說出真相的故事,或許是在批判這位神父所遵守的這項「契約」,或許是呈現法律與宗教產生矛盾時的可能性。後者則是一個自己想辦法尋找證人來洗刷冤屈的故事,影片本身則是抑鬱至極,大抵可以說貼近於被冤枉者的那種心情吧。審判在後面這部片中微不足道(因為甚至還沒有進行審判),但這種調查無疑跟司法制度有強烈的關係,希區柯克也承認這個故事大概有將自己對警察的懼怕給投射進去。總之,這部片可以考慮不放映,因為它與其他同樣處理辦案過程的影片在本質上差異不大,我也說不出捨彼求此的理由,可能是,希區柯克的影片比較好看吧。
吉布森(Brian Gibson)的《危險機密》(The Juror,1996)我印象也不深了,看了DVD殼上的簡介,甚至懷疑自己有沒有看過:「Demi Moore stars as Anne Laird, a struggling single mother who impulsively agrees to serve on a jury, hoping for a little excitement in her humdrum life. But she’s forced to sacrifice the truth to save her son from the mob’s seductive, psychotic enforcer.」從簡介看起來,應該是在探討陪審團制度的公平性吧。盧梅有一部精彩的影片,直接就是將審判程序拉到陪審團最後的決定過程中,我還是把它放到下一種類別中,所以稍後詳述。不過他另一部稍晚的作品《驚心誘惑》(Guilty as Sin,1993)講的是美麗的女律師不小心愛上她的委託人——一個被控謀殺有錢老婆的花花公子這樣的故事。到底影片有多少涉及到法庭,我也說不上來,因為我試著看了半個小時不到,實在看不下去,演出拙劣、人物平版,故事不真誠,影碟的翻譯也糟糕,盧梅的基本功力或許受到年紀影響,頗有指摘之處。我摘錄一下《Time Out film guide》(第11版)中對本片的評論:「Though the tile suggests a Jagged Edge-style thriller, Lumet has a taste for weightier courtroom dramas. Audiences expecting a legal thriller will get something deeper and darker, but if they stay long enough, they’ll also get what they came for. Jennifer, an ambitious lawyer with a killer instinct, meets her match in David, a ‘ladies man’ and alleged wife killer. Locked in a dangerous game with her seductive, manipulative client, yet bound by the rules of confidentiality, she slowly realizes she was chosen for a reason: David knew he could push her buttons. Lumet and scriptwriter Larry Cohen emphasise the erotic tension and psychological cross-currents sparking between the couple.」
至於派庫拉(Alan J. Pakula)的《無罪的罪人》(Presumed Innocent,1990)好像是在講…(本來還沒看過這部片,但剛剛想一想還是把片子看了一遍)就像一些電影指南講的那樣,是一部蠻精彩的片子,講述一個檢察官如何從一件原本該由他負責的案子最後成為該案的主嫌。剛看完時我也不疑有他地認定是不俗的作品,但細思量後,覺得作為一部偵探性質小說的改編,它漸次地揭露案情實屬必然,可是編導決定使用限定觀點的方式,讓敘事僅就主人公的觀點來呈現,這就會造成「欺負觀眾」的作法,並使得演員的演出有前後不一的矛盾,即便編導有借主人公之口不斷地提醒我們法界的一些「規則」以澄清或減低一些不合理設定,但很多細節只要稍做推敲就知道存在問題。不過或許我太多心了,畢竟一般觀眾應該難以察覺這一層問題。反正既然也算是一部頗出色的商業片,又何妨?
接著便要談到以訴訟為影片主體的影片,還真不少。可惜的是,在我所看過有限的作品中,我個人非常中意由周防正行導演的《就算這樣也不是我做的》(2006)與增村保造的《妻之告白》(1961)。前者非常有耐心地且寫實地呈現一場性騷擾的訴訟,過程中沒有一絲觀點上的偏頗,導演真的有想做到忠實的野心;後者則是透過女主角被控謀殺丈夫的訴訟,像是一次精神分析般將她某些深藏的創傷給展示出來,雖然這種題材大有替代的作品,不過本片除了有若尾文子的美貌跟不俗演技之外,增村也在節奏上表現突出,而在寬銀幕構圖上以及黑白攝影的質感上也有令人驚豔的表現。
霍布利(Gregory Hoblit)的《驚悚》(Primal Fear,1996)無疑已經成為法庭電影的經典之一了,當然這部最後以被告為精神分裂症告終的案件是將愛德華‧諾頓這位演員呈現給了觀眾,只是編導對於這種在刑案中不少出現的例子的批判意圖也頗明顯;否則就是他們對於觀眾的嘲弄是這般的明確。普萊明傑(Otto Preminger)的《桃色血案》(或譯「一宗謀殺的解析」,Anatomy of a Murder,1959)當年似乎是因為在呈現訴訟過程時太過露骨而引發該片與電檢之間的周旋。我承認對這部片的印象也所剩無幾,大抵是一些詹姆斯‧史都華(James Stewart)在法庭上的表情之類的。重新讀一下電影指南的說明,原來可能就是太過「寫實」以致於不容易留下烙印:「One of Preminger’s most compelling and perfectly realised films. A long,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efforts of a smalltown lawyer to defend an army sergeant accused of murdering the bartender who, it is claimed, raped his wife, it’s remarkable for the cool, crystal clear direction, concentrating on the mechanical processes and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s guiding the trial, and for the superb acting. Chilling, ironic and skeptical, it is far less confident in the law than most courtroom dramas, which makes one suspect that it was this probing cynicism rather than the ‘daring’ use of words that caused controversy at the time of release.」(同樣摘自《Time Out Film Guide》)。懷德(Billy Wilder)的《檢方證人》(或譯「情婦」,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1959)記得是有一個出乎意料的轉折,就像他經常在他的黑色作品做的那樣。幾位演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錯過會很可惜,因為即便我幾乎忘了影片在講些什麼,但我依舊記得勞頓(Charles Laughton)跟戴德莉(Marlene Dietrich)在辦公室裡的對手戲,那射在她臉上的刺眼陽光。希區柯克除了前述兩部作品之外,《淒豔斷腸花》(The Paradine Case,1947)姑且不管希老自己的興趣點所在(那一句女主角在被捕時說的話:「我想我不會回來吃晚飯了」),他在訪談中提到的一個鏡頭可以看得出他仍舊相當著迷在將某種「感覺」透過不俗的方式展現出來,光是這一點,就值得看一下到底是什麼不凡的「感覺」,其實也許希老自己解釋成味道什麼的,但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法庭感」。
《控訴》(The Accused,1988)的故事應該都耳熟能詳了,以致於我到底有沒有看過都沒有印象了。《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1993)的冤獄案也是朗朗上口,他對於「成長」主題的表現大概是現在在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吧。《失控的陪審團》(Runaway Jury,2003)出乎意料的內幕令人難忘,無怪乎動用這麼多大「卡司」。史萊辛傑(John Schlesinger)的《逍遙法外》(Eye for an Eye,1995)可能會一如過往地「緊張」,不過題材本身一直吸引不了我好好把它看完,講述一位母親經歷(透過電話)了自己女兒被姦殺的過程,但法律卻給了犯人緩刑,這讓她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審判犯人,簡單說,也是一個關於私刑的影片。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有兩部片也從蠻多地方論及到法的問題,《白色》(Trois Colours: Blanc,1993)或許還太抽象,我想談論平等這個問題不確定能否送到觀眾的心裡;不過,《殺人短片》(Krótki film o zabijaniu,1987)的中對法的呈現就相對明顯得多。只是從今天的角度看來,會不會覺得他在使用攝影機濾鏡太氾濫而迷失了他原本想要搗入的犯罪本質?盧梅除了前述的影片之外,這裡還準備了兩部,剛好可以證明他對這種題材的偏愛以及他的系統。一部當然也成為經典的《十二怒漢》(12 Angry Men,1957),在這裡,十二位憤怒的陪審團最後慢慢達到一致而推翻一開始的決定,巧妙地將案情整個發展重新濃縮在這一次長達將近兩小時的討論中,節奏控制極為出色;米哈爾可夫(Nikita Mikhalkov)於2007年所重拍的同類作品也不見得有超過的跡象,加上後者又更多觸及到政治問題,所以我想那又太過複雜了,所以就從這份片單中除去了。盧梅的另一部片是《判我有罪》(Find Me Guilty,2007),這也是一部我已經全然沒有印象的影片了,一位黑幫老大為了不出賣同伴以求取較短的刑期,反而選擇了自我辯護的方式爭取自己的清白。印象中好像在訴訟過程的呈現上有些不合理之處,應該說有明顯不合理,不過又據說本片是實事改編……總之,我感覺在這部片中,盧梅才是那位「angry man」。
當法律碰上了更大的機制,訴訟就會反而變成小兒科了。《朗讀者》(The Reader,2008)曾第一時間就躍上了這份清單,但後來又一度被我刪去。不過在與表哥聊到我在準備的這份清單時,他也馬上就想到本片,因為我們一致認為安排在影片中間的這場訴訟有其重要的意義,不是只是對於這個角色以及這個故事來說,而是這部片本想提問的大機制。是在這裡對那位當年負責看守教堂的大門,在「盡忠職守」下使得300位猶太人被活活燒死的女子對她的罪愆感到疑惑的呈現,才讓我更進一步體會納粹(或者可以說「法西斯主義」嗎?)的作為及邏輯。所以,即使這個訴訟需要花點時間慢慢導入,但我卻相信它非常值得觀賞。相反地,柯斯塔-加華斯(Costa-Gavras)的《父女情》(Music Box,1989)一如他過去的政治影片一樣流暢、有張力,本片同樣要講述關於法西斯的暴行,可是觀賞後細想,卻同樣會發現影片(或編導)的那種偏執。一位女法官被自己的父親要求為他辯護,這位在美國居住超過40年的匈牙利人被控當年撒謊以取得的美國公民身份是無效的,謊稱是農人的他當年其實是匈牙利納粹的一份子,且還是最惡劣的兩個之一。女兒憑藉著對父親的愛,打贏了官司,但卻也在最後才知道他確實有罪,最後,影片的回馬槍是讓女兒告發了自己的父親。影片拍在俄共解體前夕,大概不是偶然。
最後還有兩部片,一部是野村芳太郎的《事件》(1978)以及卡耶特(André Cayatte)的《審判終結》(Justice est faite,1950)。前者是在清查我的影片收藏無意間發現它原來也是一部關於訴訟的影片,影片的男主角被控殺害老婆的親姊姊,而他本人也承認犯案,但隨著訴訟展開,一個關於四角關係的過往被揭開了,直到最後法官發現犯人並沒有主動殺人的行為而給了他一個相對輕的刑責,而那時,男主角居然微笑了,這大概是影片最大的敗筆吧。本來前半段對於「回憶畫面」的消音處理頗有趣,但後來閃回開始失去這種嚴謹性,導演並沒有為這些影像在觀點轉移或者關鍵呈現時提供緊密的意義;再者,片中的兩次裸露也有刻意之嫌;當「事實」被揭示後,人物間的過往行為,也明顯有對不上號的感覺。在在說明導演果然是一個「小導演」,而撰寫劇本的新藤兼人也脫不了關係。這部片剛開始看,讓我有種可以取代《就算這樣也不是我做的》的錯覺,不過看畢後至少覺得仍有可看的價值。而拍攝法庭戲出名的卡耶特這部片我個人也沒看,從劇情敘述看來,可能是一部也將重心放在陪審團上的影片:「一名女子被指控殺了她生病的丈夫,儘管種種跡象表明她只是為她病危的丈夫實施了安樂死,但另一方面她對丈夫有不忠的行為,並且可能有經濟方面的動機存在。七名陪審團對這位女子的生活情況進行了調查,最後進行判決:四票對三票判她有罪。影片細緻入微地展示了法庭的判案過程,以及其中所有的矛盾衝突。影片的重點放在了陪審員的個人情感上,這一因素對判決的影響顯然比事實大得多。」
我再總結一下這份片單:
《審判》(The Trial,1962,Orson Welles)
《周圍的事》(ぐるりのこと。,2008,橋口亮輔)
《造雨人》(The Rainmaker,1997,Francis Ford Coppola)
《義勇急先鋒》(…and Justice for All,1979,Norman Jewison)
《大審判》(The Verdict,1982,Sidney Lumet)
《法網邊緣》(A Civil Action,1998,Steve Zailian)
《懺情恨》(I Confess,1952,Alfred Hitchcock)
《伸冤記》(The Wrong,1957,Alfred Hitchcock)
《危險機密》(The Juror,1996,Brian Gibson)
《驚心誘惑》(Guilty as Sin,1993,Sidney Lumet)
《無罪的罪人》(Presumed Innocent,1990,Alan J. Pakula)
《驚悚》(Primal Fear,1996,Gregory Hoblit)
《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1959,Otto Preminger)
《檢方證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1959,Billy Wilder)
《淒豔斷腸花》(The Paradine Case,1947,Alfred Hitchcock)
《殺死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1964,Robert Mulligan)
《控訴》(The Accused,1988,Jonathan Kaplan)
《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1993,Jim Sheridan)
《失控的陪審團》(Runaway Jury,2003,Gary Fleder)
《逍遙法外》(Eye for an Eye,1995,John Schlesinge)
《殺人短片》(Krótki film o zabijaniu,1987,Krzysztof Kieslowski)
《十二怒漢》(12 Angry Men,1957,Sidney Lumet)
《判我有罪》(Find Me Guilty,2007,Sidney Lumet)
《朗讀者》(The Reader,2008,Stephen Daldry)
《父女情》(Music Box,1989,Costa-Gavras)
《事件》(1978,野村芳太郎)
《審判終結》(Justice est faite,1950,André Cayatte)
後記:
想一想,雖然能讓我更加專注地思考這類影片,不過整理這些法庭電影的過程中,老實說,收穫並不多。
看一看漫畫《裁判長!這個案子判四年,如何?》就知道(當然不見得要參考這部漫畫),所有的案件本身就具有戲劇性,因為是犯罪,不是「日常片段」,再加上人們對罪行心理的好奇,法庭影片有天生的資本。
那麼,創作者如何不去販賣案件的戲劇張力呢?想來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這些影片賴以獲得票房的方式,無非就是1.增添戲劇性,靠張力來號召;2.批判體制,利用人們的共鳴,但前提仍是戲劇性;3.同情心,這點多少也帶有批判的意味;4.勵志,多也跟批判性結合;5.形式處理,這點至少沒那麼低級,但確實也難讓人做到。看來,除非是對「法」有另一層體會,並且將法置放於影片的次要地位,如此一來,比較容易達到不廉價出售「法」的行為,像是《周圍的事》跟《為愛朗讀》,可惜後者多有瑕疵,破壞了某些很棒的立意。
這麼想一想,威爾斯的《審判》由於賣的是一種對「法」進行質疑的「精神」,它比較特別,當然啦,它的形式也是玩得非常暢快的。至於周防的《就算這樣也不是我做的》,大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最不去拋售法的天生魅力的影片。同時,它的節奏也是保持與掌握得十分出色的影片,一部非常沈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