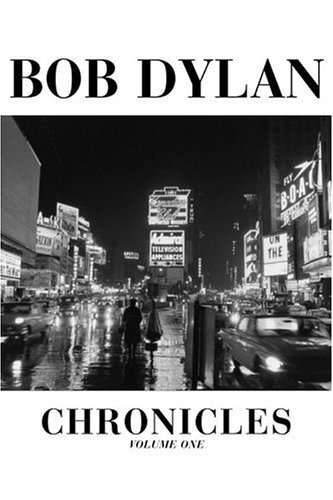像一块滚石
最初得知这本《纪事:第一卷》的出版,是去年圣诞节上午在旧金山声名显赫的“城市之光”书店橱窗里看到它。我当时急于冲上那个传奇的小阁楼,所以竟然没有去找来翻翻,不过还是一直记得它醒目的黑白封面竖立在亨利•米勒和艾伦•金斯堡之间。这种摆放体现着书店作为美国当代文化地标的位置,同时也再次宣布了鲍勃•迪伦超越了歌手的社会价值。
此前的三年间,我看过两次迪伦的演出。和二十年前最早听到的《在风中飘荡》相比,他的音乐已经不是近半个世纪前简朴的木吉他+口琴+吟唱的民谣了。乐队成员们身着红配黑的晚礼服,精纯的技艺融合着多种美国民间音乐——此种声音作为一种气氛,其显要性已经盖过迪伦的词作,重新包装了他的个性。当现代和根源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年月继续碰撞,当所有的旧作被另一代人试图解读,迪伦已经不可能变得更深奥了。于是他自然开始走向神秘。
虽然迪伦每年都有百十场演出,但想必都和我经历的一样,在台上一气唱十几首歌却一言不发。在台下,他素以低调著称,以至于偶尔在杂志上看到他愁眉苦脸的宣传照都象是面对狮身人面像。相反,关于迪伦的专著已经五花八门,翻开任何一本还算正规的摇滚音乐史或是民谣音乐史,他也会统领不小的篇幅,即便是在严肃的文化或历史书籍中,他的出现也丝毫不令人奇怪。这些书籍,一类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照例会提起我们已经读了一百遍的纽波特民谣节和摩托车事故;另一类则是为了完满文字的结构或功能,把他塑造成格瓦拉式的人物,屹立在那个榜样的年代。
还有什么比一本自传式作品更能拨云见日的?这想必也是《纪事:第一卷》成为去年最畅销自传之一的原因。同时期发行的那本重达三点八磅的大书《歌词:1962-2001》就逊色得多——人们早就知道他唱了什么,他们想知道的是:他是谁。
了解这本书的直观方式是听听西恩•潘朗读的有声版本。这位和迪伦一样愁眉苦脸声音沙哑的演员忠实体现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叙事性。迪伦再次展示了他讲故事的天份。只不过这次的故事不含有任何象征和隐喻,它漫长、沉稳而通俗易懂。无论是街道井盖里散发着水汽的平凡街景,抑或白宫被校车团团围住以防止抗议者冲击的动魄时刻,都在不经意间闪过我们的眼帘。
迪伦叙事的口吻很难说是回忆,因为他不会用近半生的经验去评说一切,也从不感叹,这使得书中迪伦的年龄变得模糊。书中的众多观点喜好,你不知道属于当年的他还是如今的他,只好认为他是个数十年如一日顽固不化的人,没有青春期也不会衰老,死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叙事节奏是缓慢的,场景却是蒙太奇式的,在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跳跃,在不同的城市间跳跃,各式角色走马灯般上场——当然,也会有特写镜头。读此书,就如同是花一整个下午在咖啡馆听他瞎侃,想到哪说到哪。但是,请不要把这本书与随笔集甚至博客混为一谈:我相信这是迪伦此生唯一的自传性作品。
自然,迪伦一生所致力的音乐成了此书的线索。只是那些期待着歌词释义的读者注定要失望。因为连他自己都说,拿起当年的歌词会认不得,甚至不能想象那是出自己手。好在此书确实用许多篇幅细致描述了某些专辑的诞生过程,细致得像是录音日志。他还饶有兴趣地分析在八十年代末是如何革新自己的音乐的,不厌其烦地讲解自己的技术理论。看得出,这个人写得津津有味。
美国资深音乐史学家格雷•马库斯曾经以《看不见的共和》为书名来诠释迪伦在民谣音乐方面的出色贡献。而在迪伦看来,此称谓体现了民谣音乐本身的平凡和广阔。《纪事:第一卷》虽然远不能当作美国民谣音乐史来读,但从这位继往开来者的经历中,还是可以管窥。迪伦开篇就用了近百页的篇幅来描写纽约格林威治村的风情,刻划众多远不如他著名但他视为前辈的艺人。于是,你读了一百页之后,还没有找到一首迪伦的作品,而他还在刚刚开始考虑是否进行原创。 更进一步的是,这本书描述了这位时代骄子完整的精神家园,特别是他所受到的各种影响。除了提及数以百计的音乐家外,普希金,福克纳,迈尔维尔,艾略特及垮掉一代等大批作家都被他一一点评。关于社会,他并不热衷描绘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但却乐于讨论废奴运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报章,还有我们早已遗忘的乔•希尔等人。他对爵士乐心存好感但喜欢更直白的表达方式。他大加赞赏希普—霍普音乐家Ice-T, “公敌”,N.W.A.和Run DMC, 称他们为“都是诗人,知道如今是个什么世道”。 这也许正应了爵士大师塞隆尼斯蒙克对他说的话,“我们搞的都是民谣音乐。” 在了解了这个人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后,你不但会明白他为何会被推上一个时代的浪尖,也会理解他在那个时代退潮之后还能够继续唱了三十年的动力。 “民谣音乐是一种更辉煌的现实。它超越了一切人类的理解,如果他呼唤你,你就会消失,被吸入其中。我在这种并非由具体的个人而是由原型创造的神秘中感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从人性中提取得栩栩如生的原型,哲学的形态,每一个坚强的灵魂都充满了自然认知和内在的智慧。每一个都值得一份敬意。” 他所说的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完美的再现。没有高潮,但也没有一页能容你匆匆跳过。
其实,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出发,《纪事:第一卷》的意义之一都在于消灭迪伦所谓“抗议歌手”或“时代代言人”之类的形象。他在书中多次对此类头衔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于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场面,算是有趣的例子。从一开始,迪伦就没有体现天降大任的使命感。他乐于描述家里的厨房和孩子。即便是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这样的大事,在他的眼里死去的也只是“一些父亲,留下他们受创的家庭”。“我从来也没有超越现实中的我——一个民谣音乐家,带着朦胧的泪眼走进灰蒙蒙的雾气,写出一些浮动在光晕中的歌。……我不是一个导演神迹的牧师。那会令每个人发疯。”
迪伦自己在形容自己的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时说:”我不是反流行文化之类的,我也没有野心掀起事端。我只是感觉主流文化虚弱而且捉弄人。就象是窗外天寒地冻,你必须穿着笨拙的鞋才能走出去。我不知道我们身处何段历史也不知道真理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关心这些。如果你说的是真理,那很不错。如果你说的不是真理,那也不错。民谣歌曲教给了我这些。”显然,一代歌手内心还是桀骜不驯,但他知道自己的处境。
迪伦是稳重的,但你还是能从他闯荡格林威治村的故事中读出他的热情。当他叙述个人和家庭隐私受到的猖狂侵犯时(想想看,通向“抗议王子”家的路线图已经贴满了五十个州),溢于言表的则是愤怒(再想想看,他甚至不得不准备好枪支)。更多的是他不动声色的睿智和癫狂。他甚至不断冒出不动声色但却惊为天人的文字。比如,“有一次我放上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它照例旋律丰富,但是,它听起来还是象许多个嗝儿以及其他身体功能的释放。” 显然,老头儿的某些思绪还是一个谜。
对于迪伦的乐迷来说,这本新书是不可或缺的。虽然还够不上百科全书,但它毕竟能给各种推敲猜测以官方的结论,诸如迪伦名字的由来和61号高速公路的意义。它最终是一些地点,人物和场面的集合,读者必须自己去创造索引。他喜欢与人互动,所以在他笔下,与美国杰出诗人阿奇伯尔德•麦克利什、流行歌手小弗兰克•西纳特拉和U2主唱波诺各色人等的会面,都写得耐人寻味,而他在那家挂着毛泽东和李小龙海报的无名路边小店里遇见的奇人孙派,带来的完全就是一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风暴。他喜欢描绘城镇和路途(连他的每辆座驾都型号齐全),于是我们就熟悉了纽约、纳什维尔、新奥尔良、伍德斯托克和明尼苏达的那些大小城镇,还有象纽约民俗中心这样有趣的地方。他不时也会透露一些传奇式的经历,比如涉过水深齐膝的沼泽去伍迪•古泽瑞家去取后者未发表手稿的故事——当他特意提到Wilco在四十年后终于拿到那箱手稿并且重新演绎时,你触到的是美国民谣音乐不息的脉搏。
迪伦说,“我认为我找寻的是自己从《在路上》中所读到的——寻找伟大的城市,寻找速度,及其声音,寻找爱伦•金斯堡所称的 ‘氢气点唱机的世界’。” 《纪事》不可能取得他那些歌曲的声望,也不会超越那些划时代的著作,原因仅仅是它选择了包容而不是进攻。 也正因如此,他经历的一切终于成为他所寻找的一切。无论同意或反对这一点,你都会期待第二卷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