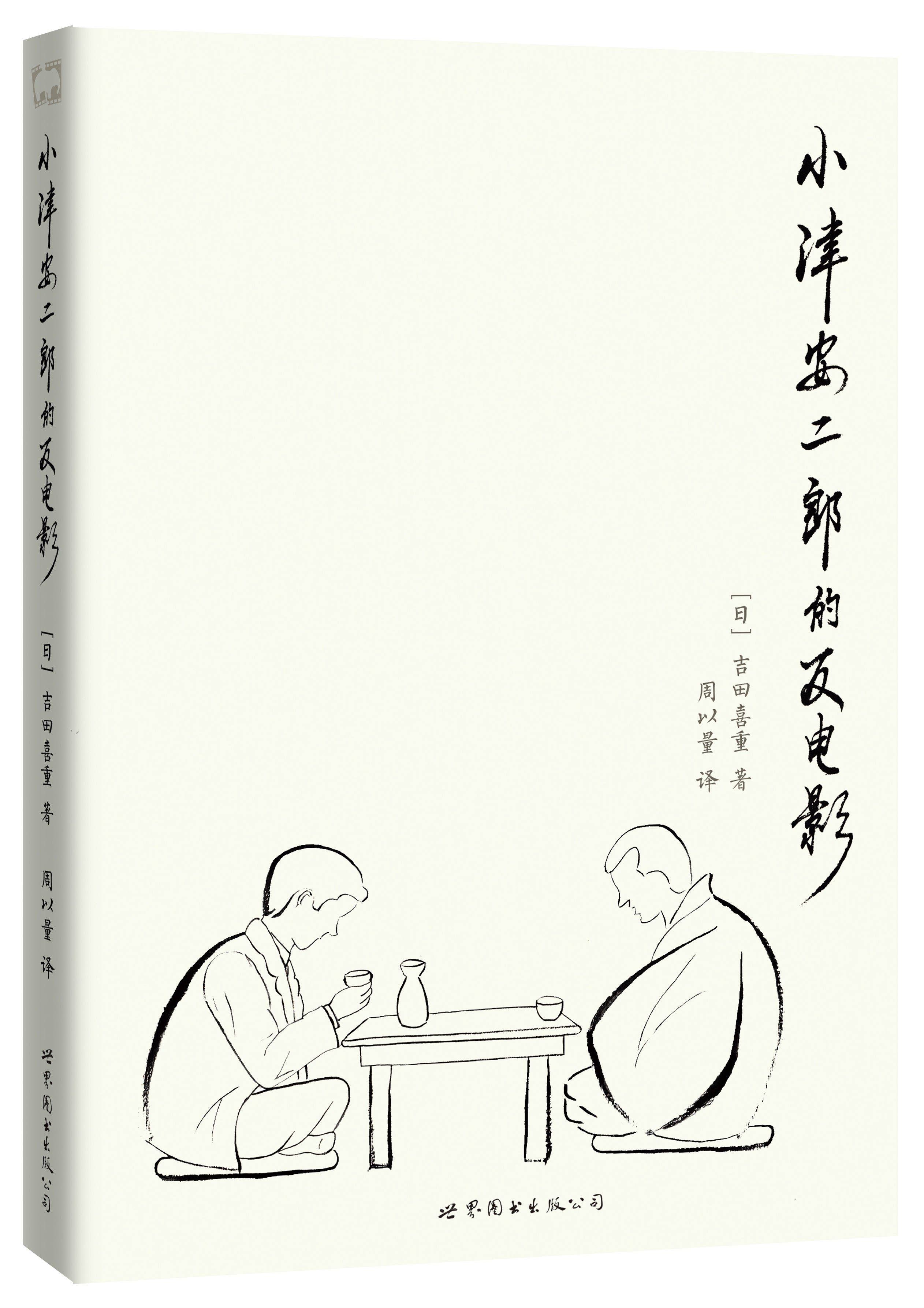不敢问小津的,千万别问吉田喜重
小津安二郎到底反了什么?
——不敢问小津的,千万别问吉田喜重
制约的书名
一本书的书名就像一篇论文的标题,左右了全书的基本论调,所以选择好的标题很重要。吉田喜重的《小津安二郎的反电影》可说是作了一个负面的教材,因为首先他得在书里头讲清楚到底“电影”是什么,然后才能谈小津在“反”电影的什么。这个前提自然陷自己于不义了。进而,为了要谈小津的“反电影”,估计就要牺牲掉小津“不反”的部分,这就叫人好奇,小津的电影真有这么多“反”的处理情况,还让吉田能写出一本书?阅读吉田这本书,无疑充满了这些焦虑,这种焦虑感也都怪书里头传达出来的负面情绪。
但还有一个前提挺棘手的,自然还是翻译的问题。我在此先举一例。书中引用了小津对于日本真实生活的“非电影化”的感触:“当我们进入家门时,打开格子门、坐在玄关处,解鞋带,向这样的情景,无论如何都会给人带来迟缓的感觉”(P.27),并补充说小津这番话多少引起一些争议,吉田为他作的解释是“小津明知这种说法十分危险,但他还是阐述了其对电影的热爱之情,即便电影与现实相隔,只存在于银幕之上。由此可见,小津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P.28)
小津这段被引用的话应该是没有被曲解,因为在其他处(比如《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就有看到类似的见解,不过,尽管如此,小津仍旧有办法转化这种因迂回造成的“迟缓”,比方说在《秋刀鱼之味》中,让父亲回家脱鞋、挂帽子这种戏,在有女儿、没女儿迎接以及由媳妇迎接之间不同的情况所产生的微妙差异,来体现人物之间的依存关系,而这个关系则引动了在与不在对人物造成的情感状态;而在《早安》里头,那么一次的玄关脱鞋戏,居然是某一个人物跑错家,以为回到了家,但其实跑到邻居家这种乌龙状况,把停留当作笑料噱头的舞台。这才是小津在现实中必须反电影的前提下又转化成纯电影化的功夫。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不也都需要在玄关处脱鞋?
然而,对于吉田替小津作的解释,看起来似乎不太像是小津会有的情绪,尽管这是吉田个人的诠释,但未免也太不自然。基于手边没有日文版本可以参照,只好拿由两位日本人翻译的英文版来参考,既然是日本人自己翻译的,应该在理解上也不会偏差太多才对。在英文版的相同段落中,感觉似乎比较“正常”些:“小津对摄影机制的绝望之深,以致于他坚持电影中被描绘的世界应该独立于围绕着它的物质世界而存在。”(P.20)这也是为何后来一些要钻牛角尖批评小津的反对者,老是说小津电影的世界根本就不同于真正的日本日常,这倒是大实话,完全符合小津在这里的诉求。然而小津真正精采的也在于此:透过极端戏剧性的设计,却流露出异常现实的印象。比如在《彼岸花》里头,观众可能会对山本富士子演的佐佐木幸子对佐分利信演的平山涉用计的戏显得太不自然,不打紧,看看平山涉与他的部属近藤庄太郎(高桥贞二饰演)关于“Luna”酒馆的系列噱头,是非常细腻的现实再现,更别说田中绢代饰演的母亲清子,在一看到先生买回来、参加婚礼用的手套、领带,也听到先生表示即使不情愿还是得参加女儿婚礼的话之后,立马冲到二楼跟女儿传递这个好消息,那种移动,带点滑稽,但你在看到这一幕时,绝对是笑中带泪。戏剧性是小津建立起他再现世界的利器。
小津反电影吗?
在这个前提之下,吉田提出了哪些小津“反电影”的方式呢?我这就先剧透一下,吉田在这本书的书写,无疑泄漏了他其实不懂电影这个严重的致命伤。
在前两小节“空气枕的视角”、“匿名的非人称化的情景”,吉田从“不可见”来讲述小津的反电影,前者是透过《东京物语》开场不久,老夫妻关于空气枕的话题中,这个被提及的重要道具始终在画面上是缺席的;而后者同样指《东京物语》的一场戏,是二媳妇纪子在招待(没人有空招呼的)公婆,在一个高处(东京铁塔?)为公婆指出他们的孩子们各是住在哪里,而画面上仅能看到他们眺望的背影,东京影像也是缺席的。吉田以为这是因为小津不相信电影能如实重现被摄物的能力(P.12),当然也就是“反电影”啦!
可是,这两例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去谈。以空气枕来说,它本来就可以不需要被呈现,因为这场戏更重要在于传达人物性格,老父亲下意识就对妻子严厉了起来,姑且不论说其实空气枕实际上就在他的行李箱里头;其次也预示了将来对太太病情的忽视,特别是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再有,则回应了他在太太死后的感叹:“如果能再对她好一点就好了。”吉田说的也没错,这里是透过“不在场而引起的反向思维”(P.6),如此一来人们会更注意到空气枕的存在,可是,引起观众注意的理由呢?然而,重点是,“电影”从来没有狂妄到自认可以再现一切情景,画面中的窗窗框框、各式遮蔽物,都能将物体或部分或完全隐藏起来,更别说景框拍不到的场外,被暗示、被提及,却不在画面中,这是随处可见的手法,完全也不是小津的特长,岂有“反电影”之意?
另外,纪子给公婆指路的戏更无须显示,这还包括老夫妇两人在高处对着东京市区感叹说如果走散了就再也碰不到面了(P.11),这两个时间无论哪一个时间给观众看东京的鸟瞰影像都是没必要的,后面这场尤其是,对于两老来说,哪里是哪里根本不重要,而前面这场,纪子为他们指指点点的重点应该在于她与大舅子、大姑住的地方离得很远,远到还得多用一个镜头来强调刚刚那个位置看不到她的住处,住得这么远,很可能暗示了两个方面,一是亲疏情况,二是阶级差异,当然同时还响应了纪子到大舅子家的距离,让她在公婆第一天来大舅子家时,她还帮忙家事到很晚(而大姑则负责跟公婆一起聊天),但她一点都没有为难的情况;相同地,她所处的小公司忙碌不堪,但大姑一句要她招待公婆游历东京市区,她也在所不辞。因而,人物之所见本来就不是重点,而是场面之外的余味才是关键。
吉田懂电影吗?
事实上,以“反电影”的角度来说,后面那一场戏,在老夫妇感叹完东京之大这件事之后,两人缓步走起,而摄影机也亦步亦趋地跟上,这个镜头虽为时不久,但它毕竟是全片仅有的两个运动镜头之一,前一个发生在不久前,老夫妻在树下吃饭,摄影机摇过一排墓碑,才来到他俩的身影,这个运动镜头当然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虽说小津也可以跟过去一样,透过几组镜头来传达相同的含意;然而,后来这一运动镜头,才真让人摸不着头绪,因为这一跟,按理说好像要发生什么,却也还是什么都没发生,难道是想拍两老的步态吗?这也说不过去。因此这一个直击“空无”的运动镜头才真的有反电影的意味。
篇幅有限,无法为读者罗列更多例子,但有些基础认知上的差异,可能使得这本书有着各种致命伤。比如在第六节里头谈到“意义悬浮的蒙太奇”(英文直译为暧昧性蒙太奇),指出小津受到美国电影的影响,“有意识地或者说更加人为地将不同性质的影像或看似与故事情节毫无关联的镜头接起来”(P.39)但是根据吉田对这种蒙太奇的叙述,彷佛更像是俄国蒙太奇,特别是爱森斯坦钟情的“杂耍蒙太奇”的处理方式,再说,将不相干的镜头接进来也不是“反电影”的手法,这一直是广义蒙太奇的运作逻辑。为了让读者参考,英文版本是翻译成“小津有意识地插入看似与影片故事轴无关的不寻常影像,引起观众的不舒适感”(P.26)。另外,在谈到《晚春》一场戏,纪子在街上遇到父亲的朋友北川,两人的交谈中先是北川说可以陪纪子去买缝纫机针,后又说要纪子陪他去美术馆,最后,观众看到美术馆的海报,但两人却到了小酒馆。吉田认为小津“嘲弄并挑逗观众,让我们察觉到电影无非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而已”(P.93),那个觉得电影导演像是桥下取悦客人的妓女的小津,确实有可能表达电影是把戏这件事,但会想取悦客人的他绝不可能“嘲弄”观众。事实上,这里透过极大的省略,同样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北川压根没想陪纪子买东西,美术馆甚至也只是幌子,这位与年轻太太续弦的北川,很可能只是想跟纪子相处而已。裁缝店、美术馆则完全不是重点了,然而这样的处理,还是电影,而非反电影。
(原載《看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