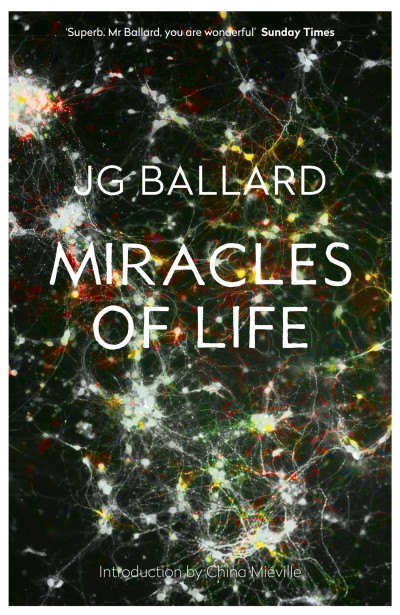从Shepperton到上海
文/小河
(上)
1930年代的Shanghai Express整个故事都发生在北京驶往上海的列车上。一等座包厢里Shanghai Lily和西化的中国女孩衣着华丽,留声机播放的旋律在整节车厢回响。电影描写的是混血军阀在北方与南方政府对抗——即便全片出现的中国话都是广东方言。我猜,这电影大概接受了临城事件(1923年的劫案,也是劫匪为了跟政府讲条件)的灵感。贯穿南北两座重要城市的旅途变成了惊险之旅。而如今我也在两座城市间运转。高速铁路却让我有眩晕感。4小时55分是最短的旅行时间。北京南站特辟这一线路的候车区,你甚至不用拿火车票直接刷身份证就能上车。这才是真正的上海特快吧。
1930年代的巴拉德没有去过北京,他最北去过青岛。不久之后便困在了龙华。其实用“困”字也许并不准确,因为那空间即便狭小,他也能在那里看到整个世界。我之所以用“困”字,也许更是基于自己的心态。巴拉德自传Miracles of Life: Shanghai to Shepperton一书是在充满油烟的狭小空间读完的——读书过程也时常被打断(因此反而读的格外快)——我在遥远的北方贩售中餐外卖,其中包括一种叫做“上海面”(Shanghai Noodels)的食物。这种食物极少有人点,反而卖不过“鸡面汤”(Chicken Noodle Soup),尽管这两种食物都颠覆了我对面条的理解。老板并不看店,资深店员们对我看书看杂志并无意见,主持大局的大厨表姐甚至会笑闹焦头烂额赶论文的朋友,“写不完带来店里写吧。”在我与排着队的现场来客、两台电话机、两台网络订餐平台打单机、收银台、刷卡机、传菜单、外卖单还有食物、软饮纠缠不休的时候,那书便被随便倒扣在前台桌面上。余光扫去,外卖店雇佣的波兰司机好奇的拿起来闲翻。是啊,生活的奇迹/生命的奇迹?书名看上去颇为励志,正是如此狭小空间里的我们需要的吧。这也让我联想到有一天,最爱与我们讲述“我儿子”种种,听我打趣朋友若干年后就是“Dr. 某某”还以为她是医生的另一位司机尼古拉斯结束我们随口几句闲聊时给出的总结——“这就是生活”。也许我是少有的先读巴拉德自传再读文学作品的人吧。在读完生命的奇迹之后正好有机会去一趟伦敦,那就去看看Shepperton吧。
去伦敦是搭火车,由北至南几乎要贯穿国境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去英格兰,同时我在疑惑会不会是我这段时期的最后一次去。平日里不觉得什么,直到想到可能马上要离开这个国度,才对车窗外的草木生出几分感情。同样是从北到南的旅行,从阿伯丁到伦敦的火车(中间的某一段是曾经的Flying Scotsman吧)只有接近大的城镇时才能搜到一点信号(也许也和我的移动公司有关,大家讥笑有堵墙就没信号)——不像现在京沪高铁的我全程3G。车程也更久,需要差不多八小时。等到窗外充满阳光的时候,我猜,就到英格兰了吧。
去伦敦之前,不免焦虑,很久没有在大城市生活,我还能应付地铁、人群、交通工具轮番换乘吗?但一到国王十字车站(这是幼年得知以及在头脑中想象过的地方)——我才明白焦虑的多余。“城市人”特质仿佛早已写入基因,我也加入了拥挤的人潮,面无表情的地铁客,在撞上迎面快步走来的人之前彼此迅速闪身。在通往深邃的手扶梯上,背着包在左侧快速路上行走。在伦敦那几天,游客般从东部Greenwich附近辗转至中心地带(是乘坐Thames Clipper经由水路进城),后来再搭轨道交通至Shepperton往返。
那是在伦敦最后一日,一个周日的清晨,我五点多起来。这一条街多是住宅和旅店,安静,整晚不曾有过住在东边时喧闹的酒吧和来来往往的警报声。六点出门,遇到一两个行人。几位穿工装裤的年轻工人——是建筑工油漆工吗?(裤子上似乎有污点)难道已经要开工?——走进麦当劳。我也跟在了他们后面。麦当劳对面即是Bayswater地铁站。走进地铁站,早班车仍然还未到。木质长条椅上,我的邻座吃着麦记盒装早餐。等了二十多分钟,搭上开往温布尔顿方向的城铁(因为基本在地面行驶)。一个阴沉的周日早上,我仍是正式打扮,一身黑。穿了连衣裙。也许因为有点早,又也许因为是阴天,在城铁转郊区火车的站台上任一阵阵风吹过,强忍着寒冷装作没事。
搭上继续西去的火车,伦敦城郊生活在我眼前逐步展开。一个个市郊小镇并没有自然地生长联结。火车线路与A打头或M打头的快速路将它们串起——Iain Sinclair和巴拉德大概都描述过那些M打头的路。(Iain Sinclair环游M25,写了/制作了London Orbital)我想象着那些郊区市镇中人们生活的自如。很快,就到Shepperton了。Shepperton如此之远,已经是这条市郊线的终点,没有牡蛎卡卡机,连伦敦交通卡都不能使用了。我在计划出行的前几日与出行前晚阅读了几篇巴老书迷造访Shepperton的游记,无一例外的充斥着Psychogeography的风格。(巧的是我刚好去了伦敦一个环境与地景的会议,他们也请了一位以Psychogeography著称的学者/写作者)这是怎样的风格呢?漫游者想东想西的风格吗?大概我应该像他们一样不那么看重地图。一位博士期间研究巴老的人所写的游记附有Shepperton照片(我得以知道巴老旧居的样貌),也有书迷明确声称自己不会给巴老住宅拍照。有一篇新闻提及巴老的房子被某家房产经纪公司出售——但屋前并没有立着“待售”的标志牌——“粉丝们你们为什么不凑钱把它买下来呢?”我不知道街名、门牌号,能摸索到吗?
一出火车站,转弯就看见一座标明Ballard Lodge的高大建筑(只是相对高大而已)——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遂凭感觉沿着B376走(这里的路段叫做Laleham Rd),这条路看起来贯穿Shepperton西部的大部分建筑群,我努力张望两边希望能发现一点痕迹——但一点线索也没有。周日上午是沉寂的,路两旁的住宅杳无声息,人行道上有人牵着狗或者推着婴儿车晨练(推着婴儿车那位也在跑步)。我听到了前方M3传来的巨大声响。走上横跨它的桥,观看快速路上飞驰的汽车。除了应急车道之外双向六车道,交通并不繁忙。快下桥的时候看到一个不知为何的柱状物,包着“有电危险”的塑料纸。继续沿着B376,两边仍是没有声响的寂寞住宅。我似乎走了很远,路过了Shepperton Green(在一篇游记中看到过这个标志),还有一座小型公园,才开始惶恐这条路没有尽头。不然就是要直接走到别的市镇了吧。巴拉德的旧居不是离车站很近吗?而且据说离镇中心也很近(这是那篇引用售房广告的文章提及的),我大概找错了方向。
找寻巴拉德的旧居并不是重点——我那时还没读过小说也更算不上书迷——重点是观察一个普通的市郊,想象一个在“国际大都市”(的市郊)出生长大的人,定居另一个大都市市郊的后半生。这样的漫游似乎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两种文化的交错重叠,也同时与时间、空间相关。我在西方世界里逼仄的“东方空间”(该店店名确实叫“东方特快”)里阅读他的上海记忆,也是在同一空间中我与朋友论及巴拉德幼年时的上海种种——朋友告诉我那时西方医疗器械的引进一大用途是毒品相关。我即将带着在西方阅读的东方记忆回到东方,寻访那些“西方空间”。而今天,如同那个当年漫游上海街头与龙华集中营的男孩一样漫游Shepperton。这样错落的感觉让我想到巴拉德自传中回忆起自己在龙华时的一个片段——“我蹲在仍然温暖的灰烬堆上,用一只弯曲的电线戳着烟灰和煤渣,想到了在霞飞路煤渣堆拣选的中国乞丐男孩。”“我当时只是想到了而已,并不给出评论,如今我仍是不予置评。”这样类比我所体会的错落感,也并不具有特别意义,同样不需要给出观点。
但毕竟来了Shepperton不是?我求助谷歌,搜索到巴老住宅的街名。此时若是直奔那条街去,应该原路返回。那条街几乎就在火车站隔壁,我现在位置的东边略偏北。但我看到了一个往北的岔路口,还是转了过去。这么走看起来需要先向北走到玛丽女王水库脚下,再沿着水库边缘向东北方向继续前进,之后,就能路遇M3,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沿M3往南走(此处的运气指的是M3旁边有可供人步行的道路),走到刚刚横穿M3的那座高架桥,再转向来时的路,就差不多到小镇中央了。不然,还可以横穿M3东侧、巴老家北侧的高尔夫球场(前提是这座高尔夫球场没有护栏可以任意进出)。之后的旅程证明了这两条路都走不通,我只好乖乖顺时针环绕高尔夫球场大半圈,重新从Shepperton东北方向绕回来。在去往水库的路上,我经过一个个精心打理过的屋前花园,还有一个小教堂——老师们领着一队小朋友穿过墓地去往主日课堂。当我在路东寻找合适角度想拍教堂的时候,一个老太太跟我打招呼,早上好。我想起了某个周日去Montrose,已经接近正午,路上老人仍跟我说“早上好”。路的尽头是水库大坝,乍一看像是小山坡,一些羊在斜坡上吃草。与之前去Lerwick可以走到水边不同,把守水库的不光有羊群,还有铁门。我临时起意没有向既定路线东边走,而是沿着水泥路向西走了走。这条路路北是水库,路南是常绿植物修建形成的高墙。墙内便是巴老写过的Shepperton电影棚。当然,也是他孩子们童年时,他经常带他们去的地方。走到一个入口处看了看,便折返。继续顺着沿水库的路往东及东北走。这条路路北是居民住宅,路南是大片草地。我已经习惯逆行(这是野外生涯唯一学会的技能),仍是靠右边人行道行走。迎面遇到晨练的妈妈和孩子——妈妈在跑步,孩子在骑小自行车。连忙走到外侧,让开孩子。妈妈跟我说谢谢——这是我到Shepperton之后听到的第二句话。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似乎走了很远,天都要开始放晴,我才又听到M3的呼啸。M3边上没有专供行走的步道,但有长势喜人的植物覆盖的区域,若是沿着M3行走恐怕得一路披荆斩棘。我过了桥,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下去。但我现在走的这条路——Charlton Ln的路南(即路右侧)没有人行步道,直接就是高尔夫球场的围栏,只有路北才有狭窄的步道,步道北部是野外丛林般的树林,从缝隙往里看去,一条小路在阴暗中蜿蜒。我只好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选择,走上Charlton Ln左边的狭窄步道,拨开各种植物,尽力离路上从背后呼啸而过的汽车远一点。我戴着红色蝴蝶结,还是有警示作用的——这么安慰自己。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伺机穿越高尔夫球场进城的预想也成为泡影。我甚至还跨越了一个桥,桥下就是刚刚来时由东北至西南的铁路。穿过铁路之后,左边又出现了民居——这里已经不属于真正的Shepperton镇上,而是属下Upper Halliford。沿着Charlton Ln走到尽头,便是A244,终于看到走了这么久不曾看到的红绿灯。过了马路,沿着高尔夫球场东边缘往东南走,摩托车们在主路呼啸而去。没多久就又看到Shepperton的建筑物,随便选了条小路往西部镇中心走。这里的很多房屋门口都立着“待售”的标志,我甚至看到了几个与传说中数年前代理巴老旧居的经纪公司相同的标志。“待售”的房屋,一路上看到了许多,不去考虑城郊更新(或是衰落?)这样的问题。这般迹象,让人感到接近目的地带来的紧张。快到镇中心的某一条街上,我甚至看到了一个亚洲面孔的老太太,在车窗中一晃而过,空中和地面奇妙的漂浮着某种植物的种子。如同柳絮或者杨絮。日头已经升高,天彻底晴了,经过一个小学(巴老的孩子在这儿上过学吗?),我脱掉外套,只剩短袖连衣裙,正式进入夏天。
重新路过Shepperton火车站,转向站后的那条街,接近了一个路口,看到了巴拉德旧居大门——这个门的颜色或许是这一区绝无仅有的吧?(恰好是我从幼年起喜欢的颜色)我尽管只看过一遍照片,就能立刻确定这里就是。我如同偷窥别人生活般不敢靠近,站在那个路口的对角方向,拍了两张路(而非大门),慌乱地闪躲着突然出现的带小孩的行人(他们是不是会常常看到鬼鬼祟祟出现在这里的陌生人?)。我绕到那座房子身后,几幅英格兰旗帜飘扬在它附近。从后边远远凝视显然无人居住的旧宅,再假装普通行人路过与它相接的邻居院落和它的正门。藤蔓包裹冬青?无人修建。院子里一些地方有草,一些地方没有。一楼二楼窗户的遮蔽情况与之前在网络里看到的照片不太一样。因为天已放晴,阳光照在叶面上泛着光亮,整个街道都看起来活泼的很。就假装行人这般路过,隔了几家,倒车的邻居,似乎讲着几句话。周日的小镇街道在正午苏醒,人们拿着要干洗的衣物去往洗衣店,小女孩在父亲身旁雀跃。还有一些走进镇中心的本地咖啡店或是连锁咖啡店。我在车站门口自动售票机买了回伦敦的火车票,走上这辆在始发站等待乘客的列车。等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车厢已经满员,听到如游客般谈论伦敦的英国口音在身旁议论。出了Waterloo车站,军乐团在车站大厅表演。我在参观了中国城之后,跳上夜车,回到北方。
(下)
当我乘坐轨道交通十六号线,从临港新城返回市中心的时候,手里捧着Crash,或者说我用Crash挡着脸。傍晚五点多,天已经黑了,我坐着四个面对面的座位中临窗的一个。从起点站滴水湖上车,那时车厢空荡,手机没电,专注发呆。当对面座位坐上一对小情侣,同时右边也坐上一个女生的时候,我专注揽着自己的背包。顺势拿出书来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视线有处可去,不至于盯着陌生人。当我开读Crash的时候,对面小情侣的对话闯入耳朵,比看书吸引人。那二位看起来好年轻(比我小多了)。女生戴着粉水晶串珠手串,其余的珠珠串串我也叫不上名字。讲着普通话,听不出口音,男生拎着全家便利店的塑料袋,隐约可见三明治和小瓶乌龙茶的相貌。直到我听女生小声嗔怒,“你不知道一孕傻三年啊。”才开始注意他们的婚戒,和他们。男生笑她与朋友发错信息,在她嗔怒后又及时扭开乌龙茶瓶盖递上。“你不知道喝甜的对宝宝不好哦?”引来另一句笑闹。我听着觉得好笑,但也不好意思径直笑,只好拿Crash做掩护,顺势从左边车窗的倒影上继续观赏。我甚至开始思考女生的职业,十个指甲都精致的点缀配饰,白色粉色是底色,似乎不适合敲电脑。那,假设她专营那些好看的串珠?我还没有想出来她究竟做怎样的工作。她就倚上先生,指着手机屏幕问,你看这是不是英伦学院风?我吓了一跳(是,从字面上来讲,我正埋头英伦小说)。看到男生从自己的手机屏幕上移动视线,点了点头。这时我头脑中又增添了一个疑惑,什么是英伦学院风?接下来偷听对话,才明白原来他们探讨的不是某位朋友的新近装扮,而是某款游戏。我为什么会这样偷听偷窥?如果给自己找点借口的话,也许是好奇,在工作日的傍晚,什么样的人会和我一同从城市边缘向市中心移动?
以上这段看起来与巴拉德完全没关,除了我拿着一本他的书装模作样之外。但我确实是当天早些时候去往滴水湖的路上,决定要将此段旅程记录在案的。与几个月前去往Shepperton一样,从上海中心搭乘地铁去往郊区新城,或可类比。这天是周三,我十点钟从中山东二路出发,步行到达南京路地铁站,再搭二号线,转十六号线。某些浦东的地名我曾经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过,复印纸被数字化的版本。是,此时此刻头顶的某些地域曾被设计成劳工新村。当天晚上的面试虽然只是按部就班,没什么为难,但仍让我给这一天做了不同于日常的安排——节省精力,专心赶路。地铁上拿着手机读论文(小声的),间隙看到飞驰列车两旁的居民区。大部分时候,我找不到中式风格的建筑。滴水湖这一带三年间已经来过两次,不算陌生,所以并未有驶向Shepperton之时的期待。去年夏天阴雨过后,天空仍一片阴霾的景象还记忆犹新,甚至当时对座男生手里捧着的东野圭吾恍若就在眼前。到了终点站,周围庞大的建筑与稀疏的人口之反差构成了夸张的效果。朋友骑着电动车来接我,当我还没从第一次乘坐电动车的紧张中反应过来之时。我们已经在几乎没有车辆的新城里飞驰,她的声音随风消散——虽然本来就是南方人讲话轻柔。而且一不留神就发现我们已经逆行——也许,这是宽阔荒芜的柏油路上更安全的做法?我们提及去年的相见,指点去年熟悉的道路,当然还有她在这里住了五六年。短短的电动车衔接之旅,是我一段时间以来,极少的与人同游。等到下午,我从朋友单位出来,再次踏上一人闲晃之旅,从与去年不同的角度看了大湖,这座人工湖修建了两个半岛——分别是北岛,与南岛。湖边某处新修了胶囊小木屋一样的建筑,大概为了可供游人过夜。同时设有长长一排公共水龙头,水泥构造,也许像军训?(其实我是联想到了野外生涯的正午在这样的水龙头下见缝插针洗衣服)这样的城郊、新城与Shepperton如何作比?虽然它确实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边缘。精心规划出来的巨型人工湖,有象征意义的中心雕塑,一颗水滴,再经过东海大桥就可以到达洋山深水港。数年前确实曾走过东海大桥,穿过白茫茫之后,忽然又见到了太阳。那样延伸下去,怎么都有种面向未来的感觉。那过去呢?大概需要重返1930年代仍是市郊的西区。
那天我第二次去新华路番禺路,从交通大学地铁站出来,看到的第一个指示牌上,番禺路被标称Fanyu Rd.,另一些路牌车站牌的拼音又标注Panyu,读音如何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那个标注着Fanyu Rd.的标牌是如此眼熟,斜三角地带的示意,我在一篇J G Ballard’s Shanghai Home(http://www.jgballard.ca/shanghai/jgb_shanghai_home.html)中看到过巴拉德的手绘图,也在档案馆里搜索安和寺路文档时看到过图样。我从淮海路拐向新华路,沿着新华路前行,试图按照原先巴拉德居住在这里的行进方式到达他的住所——在J G Ballard’s Shanghai Home一文中,直到2007年9月18日,那座房子还是一家叫做“SH508”的高级饭馆。一周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满怀好奇这里贩卖什么类型的食物?中餐?西餐?但是迎接我的,是紧闭的大门。从马路对面看去,里面似乎亮着一盏灯,但走进了看,不过是院内停着的一辆摩托车后视镜的反光。但这至少意味着,这儿仍有人。此时的房子已经和2007年的照片不一样了,“SH508”前面的“SH”已经不见,取代它的是“馨悦餐厅”和“Xin Yue Club”,围墙外面招贴着招牌菜肴,粤菜一类,还有茶点。但更凄凉的是,在主体建筑外墙右边,加筑了木牌,上面点缀着彩色的文字与图案,显示着这里有更亲民的食物——“铁板”、“冰品”。不禁能够猜想一家餐馆几经易手,却仍找不到出路。院落围栏外贴着大幅喷绘,也有午市工作套餐可供选择。番禺路上的邻居们纷纷进军饮食业,邻家亲民的老北京涮肉,紧接着是正在装修的阳春面馆。而另一方向,新华路上的邻人开了精致的饭馆——鹿园——和鹿有什么关系吗?第二次去的时候,天色已暗,那又是个雨天。我先从新华路上拐向通往当年31A Amherst正门的小巷,两排垂直的水杉(是水杉吗,怎么长得这么高?)引导着我向前走,巷子里蹲着几位白卦人士,隔壁鹿园的厨子们。一直往前走,就要到巷弄最里端巴拉德家正门(现在是院墙)的时候,他对门邻人的一只狼狗开始狂吠,我只好匆匆拍了张模糊的墙面转身离开。只听得深邃的巷弄里仍然回荡着警示的声响。就要出巷口的时候,看到一侧立着一个牌子1934 Studio,也许是什么艺术公司摄影公司,我不知道为什么单单选出来1934年,杂志业繁盛的一年。后来想想也许只不过这一区多为1930年代初期建造吧,与我臆想出来的对三十年代的怀旧可能关系不大。再从新华路拐向番禺路,去看看巴拉德家后院(也是现在的入口),我才发现院落一进门左手边的门房亮起了灯。透过铁门往里张望——这回不像之前在Shepperton那样胆怯,我并不是在窥人隐私,而不过是一个恰逢饭点儿,并期待了解餐饮业兴衰史的食客。我看到门房里点缀着两幅老照片?也许是手绘画稿?隐约显示着这里整修前的样子——看起来这门房布置得颇有品味。
番禺路508号,1970年代归属上海市仪表电讯局,据可查到的资料,上海市仪表电讯局科技情报研究所和上海市仪表电讯局专利事务室都曾在这里办公。巴拉德在Miracles of Life里说,当他1991年重访故居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国有电子研究所的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state electronics institute)。而科技情报研究所本部曾于1984年搬走,专利事务室于1985年7月14日成立——那大概可以推测,当年他看到的书刊资料大概就是属于上海市仪表电讯局的吧,或者研究所搬迁,但仍留下了图书室和书刊资料。随手检索,可以看到这个科技情报研究所在七八十年代出版过几十本技术书籍。还一直出版一份叫做《电子与仪表》的行业刊物。
新华路番禺路路口上矗立着上海影城,这一段时间,门口广告牌和紧贴建筑的条幅都宣传着一个据说讲述人们搬家、长大的华语电影。当我第一次在这个路口看到上海影城的时候,甚至是要笑出来的,1991年12月20日落成,“它是1991年上海市政府实事工程之一”,巴拉德当时来上海的时候大概还没见到过?仍是包裹着脚手架的状态?而在Shepperton电影棚制作的某些电影,会在他童年故居门口上演吧?我在上海影城一楼大厅的咖啡店读完了那篇J G Ballard’s Shanghai Home,接着出门沿着新华路向西去。有一段墙壁上刻着“新华路”的沿革。“新华路,原名安和寺路”——我想,也许我是极少数的看到过安和寺路命名由来文件的人吧。从一开始普益地产公司写信给工部局说法华路名字不好听(无法吸引潜在顾客吧),希望能改成某某大道,甚至阿谀般提议,就用工部局工务处的头儿的名字吧,以铭记他在这座城市为市政建设的努力。到工部局确定下来英文名Amherst Avenue,华文处同时给出了中文译名“安和寺路”,这里附近过去的确有一个寺,只不过不是安和寺,他们解释,这两个汉字寓意美好,安和寺与静安寺也可以互相呼应。如今,这条新华路上有裁缝铺子,手工定制旗袍与套装。也有外地口味的面馆,看起来具有某种青春或清新氛围。几家房产经纪公司,橱窗里贴着租售的宣传广告。外地人如我沿着新华路前行又折返。太阳帝国的电影里主人公骑着车也这么穿行吧。我想起来刚到上海就在网上看的纪录片Shanghai Jim,重返上海的巴拉德,从Shepperton小屋出发,到达看起来很宁静的安和寺路旧居。一个扮演他的小男孩穿过当代上海,一个很中国的回廊,背后墙面上有大型广告画——“魔奇世界”。这会不会让人想起他自己的说法,他们在上海被国际化,或者(更进一步的说)是被美国化,追看美国最新出版的漫画书。等到再回到英国的时候,奇怪的感觉?
我没有特意去寻找龙华集中营,但是也有机会路过龙华。那是去西岸艺术中心的一个城市更新展览的路上。早前就听说过徐汇滨江一带进行的规划。最新一次更是坐在一个会场围观投影屏幕上闪过的一张张效果图、今夕比较图。如今,确实是踏进了一个工厂改造的展馆。那个展馆架高的二层,图片与地图依次展示着这座城市不同区域的现在,基于过去的现在。再之前,也去过立有温度计大烟囱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并在路边看到了一个骑着三轮电动车,载母亲来看曾经的南市发电厂的女儿。她问母亲,你还记得这是你上班的地方吗?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也许是倒数第二天,走那条屡屡让我惊心的四川路,我一直幻想什么人应该以这条路为原型制作一个小游戏,那种像素小人在马路上闪躲着不分红绿灯鱼贯而来的电动摩托车,并在人行道上闪躲着塞过来的旅游广告地铁线路图。一大早匆匆沿着四川路东向南行进,随意抬了一下头,看到一块历史建筑标牌,再看一眼,普益地产公司。于是我就在上班的人群中停下了脚步。仰头看了看这座大楼。想了想投资、买地、仍矗立的或者是已消失的房屋和家。巴拉德的旧居是不是普益投资建造?算不算哥伦比亚生活圈的一部分?我根本就不知道。只知道新华路一带当时多数是他们投资建造,在巴拉德家那个路口,普益捷足先登租地的时候,工部局还提到当时他们与市政府有关越界筑路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也是同一时期,交通大学请市政府整修安和寺路,但市政府说现在没达成统一意见,没法修。再之后,那个中午,我离开中山东二路临江的那扇窗,阴天,一艘船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转弯,从我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气象信号台和东方明珠分列浦江两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