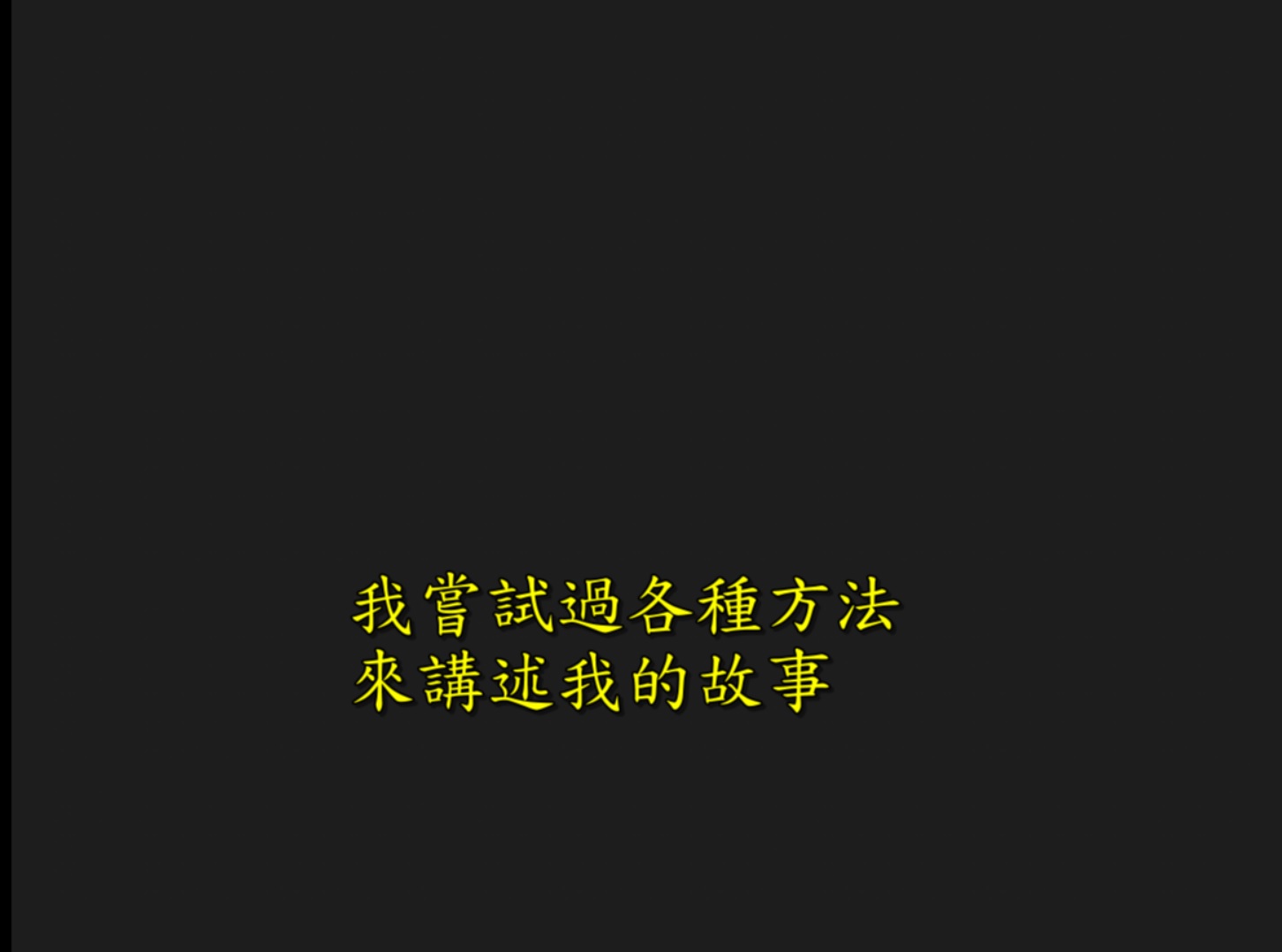拉片《歡愉》之〈面具〉
按:去年(2018)五月,我嘗試過幾種寫《在巴洛克與禪之間尋找電影的空缺》續集。各種可能性我都想過,當然,一定還有我還沒想過的樣子。但總之,後來想著想著,覺得不如寫一本新的、但依舊談小津與歐弗斯的書,那時命名為《O2O》。這本書,在某種意義上是完成了,但也可以說流產了。總之,在原本的規劃中,是想寫一篇《歡愉》(Le plaisir)的完整拉片。不過,為了寫這篇,我也試過非常多種寫法,幾乎是窮盡我所會的寫法。但是並沒有成功。以下算得上是其中一種也不成功,但寫的最多的方式。其實有寫出來的還不只這些,大概寫到第二則故事的開場。雖說字數不多,但,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文字是經過一定程度上的壓縮,儘管字少,但是真正想談的東西並不少。反正,文章沒寫完,但是拉第一則故事算是完整寫完了,所以還是可以當作獨立的東西貼出來。後來,六月份去了杭州,倒是藉由帶一些朋友花了六小時把這部片拉完,也算是彌補了我沒寫完這篇文章的缺憾。
《歡愉》開始於全黑的畫面。視覺被剝奪,留下聲音,聽覺被解放:重在想像。
一個溫和、親切的聲音之必要。為了讓人接受——商業電影致力於此:聲音在第三個故事中化成實際人物,此人無疑對模特兒的身殘脫不了干係;於是旁述者需要與之切割,「我把聲音借給他」。
聲音從想像轉為可見,如文學到電影。
黑暗中可見的光明來了,是一個舞廳的霓虹燈。
舞廳,一個充滿歡愉的場所。霓虹燈又像從四面湧來的人潮之燈塔。
人潮從攝影機的周圍湧入,攝影機也被類比為一個前往舞廳的人。攝影機於是總是放在擬人的視角。它可以是任何一個在場者。因為擬人,有時候是正常視線,有時是歪斜目光,怕是有人累了,有人醉了,有人時刻保持清醒準備狩獵。
一個人來了。為了表示匆忙、衝勁,連續不斷的鏡頭是必要的。想像一下切鏡頭的掃興。他從抵達舞廳、進舞廳、跳舞到昏倒,一共三個跟拍鏡頭,要不是因為空間限制,歐弗斯很可能就一鏡到底。但不!三個鏡頭意義上有必要分開,尤其第二個,進到舞廳後上樓的動作,承接前一個的熱切,迎向下一個的期待。上樓,一個關於希望的象徵。
不難理解歐弗斯就本片給人帶來鋪張的印象:喧鬧的舞廳由精細的布景以及眾多稱職的舞者構成了一個寫實的環境,而鏡頭,卻只聚焦在面具男子身上,且隨著他顢頇的舞步而逐漸排除了環境,除了他笨拙的身姿外無他。
對比,面具男子被抬至儲藏室,採多分鏡,每切一次都似在重新定位動力:抬上、橫移、俯瞰、抬下——尤其注意兩次俯角(前次躺著,後次被抬著),舞池的人影在他身上閃動,只嘆他自己是無福消受了。
用與剛剛目送面具男被抬走時相反的機位拍攝去叫醫生的小弟以及他返回通報舞池經理的鏡頭帶有形式隱喻:醫生根本不想照看任何需要他的人。
新的這個人登場方式華麗不如面具男但形式意義更深遠。
「但我不是為了……」醫生的面有難色、他去照看病人前與以前共舞過的女孩之依依不捨,更過份的是,在他離開後,攝影機跟著女孩回到舞池,用一種悠閒的節奏,不疾不徐地掃視舞池上歡愉的人群,那是他無緣參與的團體。
儲藏室是處置暈厥舞者的好地方。後景窄門擠滿看熱鬧的人,前景扶梯走過像是(維持秩序的)巡警之類的人。由於錯落的雜物,歪斜構圖倒給人穩定感。
小弟去拿個剪刀都要大費周章,為的是削弱醫生解開面具的時間感,或說,延長。
疲憊神情完美詮釋他這一晚東奔西跑的工作情景(舞池上的歡愉則與他無關),小弟借剪刀這個自然行動因此成了跳舞過勞老人等待被處置這一段落的某種插入式隱喻。
卸下面具花了六個鏡頭。拆解鏡頭想像它們:分鏡更像是讓攝影機化成某種機械性擺動;但整體的鏡頭組帶來印象是:拍醫生的時間與面具人相當。
實情是:前五次的跳動直接為第六個搖近鏡頭準備。這是一個逼他現形的鏡頭。遠處還有守在一旁的普黑弗絲掩面不忍睹,她是最後和面具人跳舞,也是他還念念不忘的人。
第六個橫搖加推近的鏡頭將兩個男人合一:從醫生轉到被前景扶手欄杆二度框化的老先生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轉化。背景失焦的舞女則成了這兩人合體的重要關節。
老人面部疊在馬車上。
執拗的留下與歸家的馬車,難道有所抵觸嗎?
配合隨後老婦的解說,進一步想:他的歡愉不正與回家有緊密聯繫?並非勞累而回家(他表情儘管不甘卻又安詳),是因為外出正是為了回家。家,成為他歡愉的前提。
老人在車上掛記著面具。精神已稍恢復但自知無法再跳。車開後,關窗這一小動作帶有戲劇性符碼。鏡頭帶往門口的普黑弗絲,她略搓了搓雙肩。經理把她趕回舞池,他自己則趕忙再去迎接又一輛駛來的馬車與下車的客人。
一個連續鏡頭內如此多動態:離開-驅趕-返回-迎接-前來。普黑弗絲的目送、搓肩與折返,她的憐憫被阻斷,因這裡不是裝載憂傷的場合。
也許舞池裡正有似普黑弗絲這般既能激情又有感情的舞伴,才讓舞廳如此令人著迷。
馬車停在老人家公寓前,構圖給人一種舞台感;但老人既是登場又是退場。
前景有枯枝,給人視覺上的不清爽。這是歐弗斯擅長:就要讓你不清爽。但枯枝畢竟只擋住馬車廂。且在畫面的平衡上,刻意留下左邊的空蕩,要目光可以注意一下馬、牠的眼罩、路燈,還有往下的階梯扶手。
恰恰枯枝只擋住車廂,在點出季節(無怪乎穿著單薄的普黑弗絲要搓肩了)的同時,讓人與景在形象上、在意義上相溶了。
很公平,鏡頭橫移,醫師攙扶老人下樓,他們走向左方卻成了畫面的右方,新的左邊一棟樓似是老人所居,現在,又被另一株枯枝給覆蓋。
溶接:他們漩進光影交錯的迴旋梯。
迴旋梯常為巴洛克強調,它所引導的是一種朝不透明性前去的永動(即使不動時也給人動的印象)且因為是環形不致使動態發散而形成反覆終於統一:螺旋動態完整複現了沃爾夫林歸納的巴洛克藝術五特徵。迴旋梯則是歐弗斯另一個標誌性場景。
歐弗斯藉由樓梯(不見得必須是螺旋梯;這就不完全跟巴洛克有關)的特性而抽取出最為抽象的形象:無始無終,始與終由於視覺上無法看透而他又經常讓人物已經在樓梯的半路,並且重點是就算用長鏡頭跟著他們一會兒也不見終點。
在這一小段漩渦裡,老人掛記著過去(普黑弗絲還在舞池上呢!),醫生則擔心老人的當下(有否力氣再往上爬?)和未來(妻子是否睡著而不便搖鈴?)。
「她有失眠症」拉到了某種特別當下並道出了老夫的自私與老婦的無奈:愛的施與受之不對等。
與小說不同,老婦沒有等到敲門才出來應門,而是在兩位男士走到頂樓之前便已拿著燭火出來探望。保留小說的「天吶!他怎麼了?」在片中實有讓這句話昇華。這裡還有一個細微的設計:醫師遲了一會兒才回答,顯示出對老婦等門與提問的意外。
當老婦聽到是「在公共場合暈厥」而淡然回應「是舞廳吧?」乍看與前一句驚呼不連貫。
「老婦驚呼」當屬於小說家巧思,藏著一個不明說的補全:也許老人第一次因為跳舞暈厥而有醫生攙扶回來;並且這樣才與離開時首尾呼應(向醫生要聯繫方式)。「醫生遲疑」則屬改編者智慧,立體化醫生的同時,對答之間也立體了這對夫妻的奇特——「您知道?」成了又一懸念的咒語——(這是怎麼樣的一對夫妻!)。爬樓與抵達切成兩個鏡頭:強化了行動與目的的切割。
進屋後視覺上總是被擁擠的空間、前後景的雜亂、狹小空間中不停歇的運動催促著:一種欲知又被禁制的活動,轉譯了醫生的在場又不在場。
觀眾於是很容易就忽略掉細節如桌上的食物,一個盤子上是一顆蘋果之類的水果,另一個被盤子給蓋著的盤子裡頭裝著麵包之類的食物——老婦照例給老人留宵夜(他沒吃就出門的晚餐)。
配合老婦在屋內的忙進忙出,全都是為了張羅給老人的東西:收拾脫下來的衣物、燒水讓他洗臉、暖身體、找藥給他敷。老人恰是讓老婦「活」起來的動力。她的活動也帶動鏡頭運動以增加這個空間的活力。
房間內三度再帶老人面部特寫。代表了對話的轉調。
前一次是讓老人躺下後,一個推近鏡頭,這時老婦解釋老人的行為在於「充當年輕人」;語畢,切到在旁觀看的醫生,這句話於是切開了醫生與老人。
再一次則是表示身分,老婦提到那位明星理髮店的頭牌之名,也就是老人的名字,這時又跳他臉上,那副安逸,不會知道老婦這麼晚還在為他忙碌。緊隨在這個特寫之後的,是老婦說到她如何在他頭上發現白髮時她的喜悅與他的沮喪。這也正是「充當年輕人」的開端。第三次也正出現在這段關於他白髮衰容的對話,「再也沒有女人追他」對白正對應著他的特寫;但這第三次特寫,該是妥協所致。
醫生離開,下樓動作被置放在一個歪斜嚴重的構圖中:彷彿他的三觀世界已然傾倒。
老婦追上醫生索取聯繫方式,醫生加詞:「您放心,他還能跳很久。」
老婦回答「那就好,我希望他能一直跳下去」時,眼睛直盯著樓上的家。螺旋梯的造型似把她再次捲回漩渦中。
尾聲加戲:驅車回舞廳。醫生雖是有氣無力地走回馬車等他的高坡,但下達「回皇宮舞廳」則是精神抖擻。
舞廳音樂響起,馬車逐漸遠去。
我們注意到影片省略了離開舞廳時小說中的一句描述「朝蒙馬特高地的另一端駛去」,除了要搭配大堂經理迎賓的動態之外,重要的是把「駛向……一端」這樣的印象保留在最後:醫生的馬車疾速奔向皇宮舞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