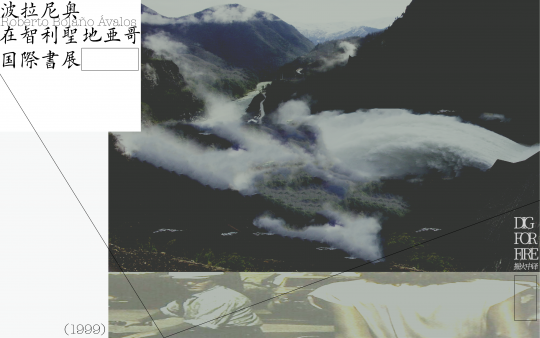掘火中译:波拉尼奥在智利圣地亚哥国际书展
译制 | anita
校对 | Angela Wu 野次馬
后期 | 瓦片
封面 | 可一
片头 | petit
策划 | 掘火字幕组
【译者前言】这是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 1953-2003)于1999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国际书展上接受的一次访谈。访谈过程中有几个诙谐时刻,比如波拉尼奥描述墨西哥诗人好友马里奥·圣地亚哥(Mario Santiago Papasquiaro, 1953-1998)的种种怪异行径,形容他“简直就像是几天前刚从一架飞碟上下来的”;又比如他谈及自己跟同伴们一起在墨西哥城偷书的经历。主持人顺着这个话题,问起他对于另外一种偷盗,即“剽窃”行为的看法。波拉尼奥回答说,文学的传世长河就是由你来我往的抄袭构成的;换言之,所有人到头来都在写同一本书。他提到自己非常喜欢马里奥圣地亚哥的一句诗:“如果我得活着,就让它没有方向,没有理智。”他甚至将这句堪称圣地亚哥本人写照的表述,用作一本书的题词,却事后被告知这句诗出自另一位墨西哥诗人之手,而不是圣地亚哥写的。莫非这也是圣地亚哥耍的一个剽窃伎俩?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波拉尼奥、圣地亚哥,以及另外多位诗人作家,在墨西哥城共同创立了名为“下现实主义”(infrarealism)的先锋派诗歌运动。墨西哥诗人、学者鲁本·梅迪纳(Rubén Medina, 1955-)是该运动的另一位创始人,他在《下现实主义:一代拉丁美洲新先锋派,或居伊·德波的“迷失的儿童”》(Infrarealism: A Latin American Neo-avant-garde, or the Lost Boys of Guy Debord》(2017)一文中,说明了下现实主义运动理念的众多渊源,其中包括欧洲“情境主义国际”先锋艺术运动(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1972),美国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秘鲁“零时”诗歌运动[1](Hora Zero),等。梅迪纳说,以马里奥·圣地亚哥为代表的下现实主义运动成员在垮掉一代身上看到了一个理想的诗人形象:梦想家、局外人,始终在冒险,始终在挑衅和对抗。这种精神特质在文初提到的那句被波拉尼奥引来用作题词的诗中获得生动的呈现;至于波拉尼奥所表达的对于“剽窃”的态度,则可以隐约从情境主义国际所倡导的艺术共产主义理念中找到回音。本文的目的正是分析,上述貌似轻松随意间提及的趣闻轶事,折射出哪些下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深层美学主张和伦理追求。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infrarealism一词的译法做简要说明。该词目前有“现实以下主义”和“下现实主义”两种常见翻译。在2017年《芝加哥评论》为该运动做的专题The Infrarealists中,马里奥·圣地亚哥的英文译者科尔·海诺维茨(Cole Henowitz)明确从语源学上将surrealism和infrarealism对照起来进行谈论。她指出surrealism的前缀 sur意为“在…之上”(over or above),infrarealism的infra则为“在…之下”(under or below)。这表明两场运动是从不同角度挖掘现实的另外一面。2017年8月一次活动中,北京大学的范晔老师也说他倾向于翻译成“下现实主义”,便于和超现实主义做一个对应。除了字形结构上的对应,下现实主义运动与超现实主义之间在理念上也保持密切对话。虽然诞生于不同的地域和年代,两场运动的参与者们所面临和所欲对抗的,都是日益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积极思考新的路径来抵御市场逻辑对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异化,以重新寻回精神的纯粹和本真。马里奥·圣地亚哥撰写的下现实主义宣言中,有一句“将炽烈的、痉挛的人生观还给艺术”(“TO RETURN TO ART THE NOTION OF A PASSIONATE & CONVULSIVE LIFE”,原文为大写)。据海诺维茨说明,圣地亚哥这是挪用了超现实主义色彩鲜明的“残酷戏剧”(Theater of Cruelty)宣言中,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的一句表达:“在剧场中注入一种炽烈的、痉挛的人生观”[2](“to restore to the theater a passionate and convulsive conception of life”)。这是两场运动在理念对话上最直白的表征之一。总之,无论从语源学角度还是理念的传承与对话上来看,本文都认为将infrarealism译成与“超现实主义”一词相对应的“下现实主义”更为恰当。
回到这次访谈,当主持人问,对你来说,诗是什么?波拉尼奥回答,我实在不知道诗是什么,只知道有一些人曾走近过诗这个现象。它应该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少年才有的心气或神态。比如,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和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 1846-1870),他们二人走过的路就是一条诗的路。波拉尼奥认为,马里奥·圣地亚哥走过的路,也是一条诗的路。据此可见,对下现实主义者们来说,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似乎比写出什么风格的诗作更加意义重大。2017年《芝加哥评论》(Chicago Review)汇集起两篇下现实主义宣言、多位成员诗作以及彼此通信,为这场诗歌运动做了一期专题。在导言中,这一期的编者兼译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指出,下现实主义诗人群体,彼此之间创作风格和主题大相径庭,难以划一,他们共享的不是诗歌本身的风格,而是与主流对抗的叛逆姿态。他们的叛逆不限于对诗歌形式的颠覆及创新,而更多体现在选择不同于传统精英诗人的社会属性和生存状态。他们致力于打破诗与生活的藩篱,将写诗融入日常生活,转化为生活方式,而非用于争名夺利、攀爬社会金字塔。他们同时拒绝依附任何体制、机构,拒绝参与建立任何圈子和权力集团。鲁本·梅迪纳为这一期专题作序,正是上文提到的那篇文章《下现实主义:一代拉丁美洲新先锋派,或居伊·德波的“迷失的儿童”》。在美学之外,他更强调下现实主义运动的伦理面向。值得注意的是, “伦理”一词在波拉尼奥的下现实主义宣言中也出现数次,其中有一句这样说:“我们的伦理是革命,我们的美学是生活:这是同一件事。” (“Our ethics is the revolution, our aesthetics, life: one-single-thing.” ) 梅迪纳进而援引福柯在《什么是启蒙》(1994)一文中的表述,指出伦理是“一种与现时性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由某些人作出的自愿选择,总之,是一种思考、感觉乃至行为举止的方式,它处处体现出某种归属关系,并将自身表现为一项任务。”[3]下现实主义运动成员们的美学追求与其对自己的伦理要求是不可分割的。诗歌形式上的激进和锋芒必然体现在诗人的生活方式与日常举止特征之中。据梅迪纳介绍,波拉尼奥及其同伴频繁地在公开场合挑衅权威作家和主流文学机构。而作为回应,从七八十年代以至于今日,墨西哥城文学文化机构都保持着对下现实主义的批判,将他们贬低为一个不可理喻的运动(“a nonsense movement”),声称由于其成员的无知、邪恶,以及生活方式的堕落,这群人根本没有能力阐发连贯的美学理念,或进行真正的文学写作(梅迪纳 2017:16)。
除了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着对抗与挑战权威的勇气,据梅迪纳介绍,下现实主义者们也有意识地践行着不断上路、远离固定圈子和权力团体的理念。比如,截止到七十年代末,多位成员离开墨西哥去往西班牙、法国、智利和美国。波拉尼奥就是其中一员。他于1977年离开熟悉的墨西哥去往欧洲,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通过从事各种职业维持基本生存,其余时间写诗。他卖过服装首饰,做过卸货工,在营地当守夜人,等等。如果赚的钱足够担负一两个月的日常开支,他就会暂停工作全职写诗。他还会通过投稿参加文学竞赛赢取一些奖金的方式获得收入。梅迪纳说,下现实主义者们很清楚,那些占据着精英特权位置、权力体系中心位置的人,时刻在阻止、歪曲和取消他人的表达,而他们拒绝与之同流。如果下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是绝不参与或创建权力团体,那么他们为此所采取的具体策略就是不出版——不通过墨西哥文学机构的官方渠道出版,或者压根不在任何地方出版(梅迪纳 2017:19)。因此,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下现实主义成员的发表或出版记录寥寥无几。无论是以个体还是团体的名义,他们经常拒绝自己的作品被列入文学杂志或作品合集。正因为墨西哥文学出版界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他们往往被批评为是一帮患有“浪漫幼稚症”的“文化恐怖分子”。但是,梅迪纳说,保持不出版的状态守卫了他们的伦理信条:比被权威力量承认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将诗与日常生活相融合,将诗视作一切反叛的核心。
根据梅迪纳,下现实主义理念的一个启发来源,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 1931-1994)创立的情境主义国际运动,而情境主义的理论基石,众所周知,则为德波自己初版于1967年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景观社会”,又译为“奇观社会”,指在消费文化的潮流下,商品通过图像、影像建构起一个幻象社会,表象覆盖真实,影像取代了真正的人类联系。德波在该书的一开头便呈出中心论断:“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情境主义国际运动成员的诸多先锋艺术实践,正是为l了打破景观对本真生活的遮蔽,抵抗资本家通过生成景观来操控社会生活。与此同时,出于对自身沦为另一道资产阶级景观的警惕,情境主义者们决心不做任何革命运动的专家、明星、权威。这恰好也正是下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所信奉的原则。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在《情境主义国际的风风雨雨》(2020)中写道,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一夜之间让情境主义国际的梦想成为现实,革命的狂欢走上法国的大街小巷,一时间,情境主义国际抵达了事业成功的顶峰。然而,他继续说,这是一个悖论,因为革命的狂欢让情境主义登上了景观本身制造的舞台,大批盲目的追随者和粉丝纷至沓来,使情境主义国际沦为一种“景观意识形态”,成为了它们自己反对的角色。基于对这个悲剧结局的认识,1972年,德波正式宣布情境主义国际解散。根据梅迪纳的介绍,下现实主义运动在1976-1977年成立之初共发表四份宣言,其中两份由波拉尼奥撰写,一份由圣地亚哥撰写。圣地亚哥版宣言中的“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拒绝把写作当成职业。”(“WHAT DO WE PROPOSE? TO NOT MAKE WRITING A PROFESSION.”) 这恰恰呼应了情境主义国际先锋艺术家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和职业化现象的批判。两场运动的参与者都致力于对抗艺术的商品化趋势,警惕艺术创作活动的景观化和僵化。据梅迪纳指出,波拉尼奥版下现实主义宣言(即下现实主义第一宣言)的标题“再一次,放弃一切”(“Leave it all, once more”),是挪用了1922年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决定抛弃达达主义时发表的宣言,后者的标题正是《放弃一切》( “Leave Everything”) 。昔日的先锋一旦被编撰成正统,登堂入室,成为自己当初的反对者,它们就必然丧失其先锋性质,而立即招致新一代先锋派的批判和挑战。而一旦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也被收录入欧洲艺术史正统,波拉尼奥这一代青年诗人就必然需要“再一次,放弃一切”。达达主义如此,超现实主义如此,情境主义国际也如此。就像波拉尼奥在第一宣言中写下的另一句话:“真正的诗人永远在自我放弃。绝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在努力与主流和体制保持距离的实践过程中,下现实主义者们尤其拒绝对国家的依附。除去超现实主义、情境主义国际、秘鲁“零时运动”这些国外思潮,梅迪纳在文中列举了几项影响到下现实主义诗歌理念的本土社会背景因素,其中就包括,七十年代中期的墨西哥文学文化界,作家及其文学活动大幅依赖于国家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导致诗歌写作缺乏独立性,损害形式创新的活力。不仅如此,出生于五零年代的波拉尼奥,亲身经历过1968年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屠杀和1973年智利政变。这一代拉美作家对国家机器的残暴无情怀有深刻记忆,而这必然会多少体现在他们的创作风格和价值取向之中。下现实主义诗人团体“浪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英国拉美研究学者Jean Franco评语)决定了他们对官方左派面向国家权力的妥协多有批判(梅迪纳 2015: 167, 174)。采访中,波拉尼奥提到智利诗人巴勃罗·德·罗卡以及聂鲁达时,就触及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波拉尼奥与主持人谈笑间聊起的“抄袭”或“剽窃”,似乎也隐约呼应了情境主义前辈们曾以话语“剽窃”为一项具体艺术创作策略这一事实。张一兵在另一篇《异轨:革命的话语“剽窃”——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研究》(2021)中,探讨了情境主义先锋艺术家们如何以“抄袭”或“剽窃”为策略,对经典文学文本进行借用或挪用,以此来实践反对知识私有化的“文学共产主义”;并通过在挪用过程中将经典文本中的陈旧语句替换为思想进步所需的全新观点和概念,达到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景观的目的(张一兵 2021: 134)。德波追溯到洛特雷阿蒙于1870年发表的关于“抄袭”之必要性的观点,将后者视作上述情境主义话语策略的原初文学语境。在他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比如,《景观社会》开篇第一句,“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全部生活,表现为庞大的景观堆积”,就是改写自《资本论》首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借由这一创造性的挪用,德波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如今已经过渡到一个被视觉表象所主导的景观社会。书中类似对历史经典文本的引用不胜枚举。关于德波对洛特雷阿蒙的追溯,张一兵概述道:
“洛特雷阿蒙曾经说,‘诗歌是为每个人创造的’,任何一首诗歌,自它被创作出来,就已经不属于作者,而是所有人可以拥有和使用的共有财富。这倒是一种诗歌共产主义。其实,洛特雷阿蒙的意思是说,在对诗歌的使用中,只要是为了艺术创新和文学观念的进步,我们就可以加以挪用和改变。… 如果说,指认洛特雷阿蒙是诗歌共产主义还有一些调侃的意味,那么,在德波的深层构境中,对已有文本的直接挪用和重构,正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文化和知识私有制的开始。”(张一兵 2021:135-136)
这样一种诗歌共产主义、文学共产主义,隐约见于波拉尼奥在访谈中对剽窃问题做出的回应。他说,文学的传世长河就是由你来我往的抄袭构成的,换言之,所有人到头来都在写同一本书。这种浪漫的文学共产主义,或许可以解读为波拉尼奥对“剽窃”,以及偷书,所持言论背后的一种深层意义。就具体实例而言,上文提到,圣地亚哥挪用残酷戏剧宣言,波拉尼奥挪用布勒东的宣言,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下现实主义者们在有意识地将历史上的经典文献带入当下真实而鲜活的语境,通过创造性引用与重写的方式,使其重获生命力。至于共产主义与波拉尼奥的关系,迄今毫无疑问的是,波拉尼奥的左翼立场鲜明。这不仅体现在他以及其余下现实主义成员有意识远离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的生活理念之中;具体到写作风格,他在诗歌与小说中展现的口语倾向,则代表着与精英文学品味、精英文人阶层的断裂。他在访谈中就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一点也不抒情。我的风格完全是平淡的,日常的。”主持人也说,他的短篇读起来像是一个人会从酒吧里听来的故事。波拉尼奥随后谈起自己非常尊崇的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 1914-2018)。帕拉对于抒情和感伤主义的拒绝,恰恰是出于对资产阶级精英文人风气的反叛。除此之外,波拉尼奥在下现实主义第一宣言中写有这么一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狂欢。每个周末他们都有一场。无产阶级没有狂欢。只有一场场带着韵律的葬礼。这将会改变。被剥削者将会有一场盛大的狂欢。记忆和断头台。感受它,在某些夜晚表演它,让铡刀的边缘变得湿润,就像抚摸新的精神那酸性的眼睛。” 这正是一份直白有力的无产阶级立场表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说完“所有人到头来都在写同一本书”后,波拉尼奥紧接着又补充道:“而这同一本书,说到底,就是‘无’,大写的‘无’,或者也有可能是小写。”无产阶级的理想是革命,是历史的前进,怎么又会转而走向虚无呢?关于波拉尼奥的历史观,值得另外撰文论述,这里仅限于提取其长篇小说《2666》中,一段涉及“抄袭”与“作者”概念的情节,来为他上述表述提供一个小说文本注脚。《2666》第五部分“阿琴波尔迪”中一节,那位因为不想做二流作家、不想成为杰作抄袭者而放弃了写作的老人,跟前来向他购买打字机的年轻作家说了长长的一段话。在他看来,真正的杰作都是被隐蔽起来的——被大量二流作家的二流作品所隐蔽。二流作品的存在就是为了遮蔽和隐藏杰作。不仅如此,任何一部二流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的作者,也就是说,在根本意义上,二流作品不是由二流作家写出来的。写下这些作品的人,脑中其实空空如也,因为他们只是在杰作创作者的指示和授意下写作。因此,他们不仅遮蔽杰作,还只是一帮杰作的抄袭者。这些二流作品,及其抄袭,最终只能将我们引向虚无:
“请注意听!凡不是杰作的作品,怎么跟你说呢?都是一个巨大伪装上的零件。我估计您当过兵,肯定知道这伪装是什么意思。凡不是杰作的书就都是炮灰,是勇敢的步兵,是可以牺牲的小卒,只要杰作的结构多次复制出来。我一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再写作了…… 我已经知道了写作是没用的。或者说,只有你准备写杰作的时候才有用处。大多数作家搞错了,要不然就是玩票…… 游戏和错误蒙蔽了二流作家的眼睛,又成为他们写东西的动力。还成为他们未来幸福生活的诺言。那是一片飞速生长的森林、一片无人能限制它生长的森林,就是文学院也不行,恰恰相反,文学院要对它的顺利成长负责,企业家、大学(培育懒汉的地方)、政府办公室、文艺赞助人、文化协会、诗歌朗诵人,等等,都帮助这片森林生长,掩饰应该掩饰的东西,都帮助这片森林繁育应该繁育的一切……
那么您会说,是抄袭吗?对,是抄袭,意思是指一切二流作品、任何出自二流作家笔下的东西,只能是对杰作的抄袭。小小的区别在于,这里说的是一种‘得到了许可’的抄袭。这种抄袭是一种伪装、一出混乱舞台上的独幕剧、一个把我们领向虚无的字谜。”[4]
访谈中,波拉尼奥在评论二流诗人,或小诗人时(主持人还顺势朗诵了博尔赫斯那首《致诗选中一个小诗人》),就表达了关于文学创作行为之渺小及转瞬即逝的观点,并批判那些向往名垂青史的作家狂妄又无知。由此看来,对于“抄袭”作为一个个体行为、集体现象,以及抽象概念,应该如何理解如何评价,波拉尼奥提供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他认为此举值得同情且不可避免。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文学的传世长河中,接纳了你来我往的抄袭,文学也是由此构成的…… 所以,这件事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根据《2666》中那段老人的独白——波拉尼奥很可能是在借老人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又时不时跳出来疏离地看待,甚至对抄袭者、伪装者加以贬斥,认为这些人只会掩饰杰作的存在,最终把我们领向虚无。基于这一认识,故事中的老人放弃了写作。“作者”究竟如何定义(讨论这个问题的经典文本包括罗兰·巴特1967年发表的《作者已死》、福柯1969年的《什么是“作者”?》等)、抄袭式挪用意味着叛逆还是平庸、诗人应投身战斗还是退守虚无…… 波拉尼奥提出了这些足以激发学者群体倾尽毕生精力去钻研探究的问题,却又无意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相反地,他只是借由《2666》中那位老人之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是解答的解答。在陈述完“抄袭将我们领向虚无”这个观点后,老人紧接着说道:“一句话,体验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说,你不能通过在图书馆看书获得体验。但是,书籍的确次于体验。”他随后讲起自己早年在一所大学的医学院停尸房偶遇一位员工,后者帮助他打破对思考终极问题的沉迷这一段经历,来进一步解释“体验才最重要”这句话的含义。借助这段情节设计,波拉尼奥提醒我们,关于意义还是虚无的这类终极追问固然有其价值,但这种由脑力劳动主导的、往往脱离身体实践的知识分子式思考,不该成为文学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的全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背后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以及作为其必然后果而出现的异化趋势。为了对抗精神异化,作家提醒我们回归生活的重要、拥抱真实经验的重要。这就再次应和了下现实主义用身体实践诗、将诗带离学院、图书馆,同人和生活一起上路的美学与伦理追求。
无论是写作实践中对权威经典文本的创造性挪用(或曰“剽窃”),还是致力于将诗与生活相结合、把诗转化为一种生活状态,由此远离权力体系的伦理追求,都是上述先锋艺术家们面对日益商品化、景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探索反抗途径过程中所奉献出的思考和实践的结晶。继五六十年代欧洲情境主义国际运动之后,诞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墨西哥城的下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为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国际案例参考。二者共同督促我们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究竟如何写作、如何生活,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被异化、商品化,被资本主义社会景观吞噬。如今,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以及外界社会文化力量的推波助澜,波拉尼奥已然成为世界图书市场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在下现实主义第一宣言的开头,他用“黯淡的星星”、“黯淡的太阳”这个意象,来喻指下现实主义所代表的存在状态和伦理追求。梅迪纳指出,infrarealism这个词的前缀infra-,由波拉尼奥取自苏联科幻作家Georgy Gurevich的短篇小说 Infra Draconis (1961)。小说讲述主人公去太空寻找被称为infras的黑色星体的故事。这些黯淡的黑色星体,因为不向外发射光芒,从星图上无法观测到它们,但它们内部却拥有足够的热度和能量。波拉尼奥用“黑色的太阳”或“黯淡的太阳”(infrasoles)来称呼下现实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因为这个意象贴切地代表了这群人的艺术和生活理想:努力呈现一整个位于现实以下的世界(an infra-world),揭示被霸权体制的光芒所遮掩的真实人间(梅迪纳, 2017: 10),同时坚定地反英雄、反偶像,不断放弃权力,不断上路,不做任何群体的明星和领袖。难怪波拉尼奥会感叹,马里奥·圣地亚哥才是他们这帮人中真正彻底践行了下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波拉尼奥没有做成黯淡的太阳,却一跃成为国际文坛一颗闪耀的明星。而圣地亚哥比他勇敢,始终未曾背离下现实主义成立之初的理念追求,始终将写诗维持为生活中的一件日常行为,而非用于个人资本生产与积累。梅迪纳也将圣地亚哥视作拉美新先锋派运动中最激进的一个诗人形象。这位“诗人中的诗人”(访谈中主持人语),将自己在宣言中写下的“拒绝把写作当作职业”和“错位的生活,不计代价”(LIFE MISALIGNED AT ALL COSTS)奉为毕生信条,直到1998年意外辞世。(anita)
文献参考:
Rubén Medina. “Bolaño and Infrarealism, or Ethics as Politics”. Critical Insights: Roberto Bolaño. Amenia, NY: Grey House Publishing, 2015. pp. 167-188.
Rubén Medina. “Infrarealism: A Latin American Neo-avant-garde, or the Lost Boys of Guy Debord”. Chicago Review: The Infrarrealist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vol 60, issue 3. 2017. pp. 9-22.
张一兵《情境主义国际的风风雨雨》,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137-143页。
张一兵《异轨:革命的话语“剽窃”——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研究》,载《文学评论》2021年第02期。第134-141页。
《对恶的思考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 | 赵德明、止庵与范晔谈〈2666〉》,2017年。https://www.sohu.com/a/161206446_240158
尉任之《盯着距离外的目标,倒退走》,2019年6月。https://www.sohu.com/a/319830235_260616
[1] 波拉尼奥所撰写的下现实主义宣言中,有一句就是:“我们继承了零时运动”。“零时”(Hora Zero):“1970年代早期由Jorge Pimentel和Juan Ramírez Ruiz在秘鲁创立的一场前卫诗歌运动。他们试图用新的艺术和诗歌改变生活,让人们从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精神异化中解脱出来,此外,这场运动还希望使得诗歌民主化、去中心化、流行化,将诗歌带到街头和普通人的生活中。”摘自《译&注|波拉尼奥〈再一次放弃一切:现实以下主义第一宣言〉》。作者:潜(来自豆瓣)。网络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819109027/ 本文所有对波拉尼奥所撰写下现实主义第一宣言的引用,译文均来自该作者。
[2] 整句为:“创立‘残酷剧场’,是为了在剧场中注入一种炽烈的、痉挛的人生观。”译文摘自《剧场及其复象》,安托南·阿尔托著,刘俐译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3] 李康译。译文来源: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106
[4] 赵德明译。
观看地址: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M4y1F73Z
腾讯:https://v.qq.com/x/page/s3316ydxnmk.html
优酷: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zMTE2NDc0N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