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损失:生活伊始的哀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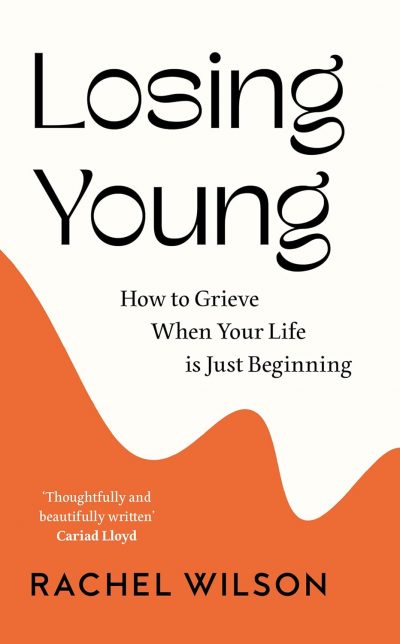
好多年前我有些计划,比如和认识的几位丧亲的朋友聊聊,再写篇文章,或者写几篇。但也仅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不过那时候确实认识几位。也在微博偶然认识了一位比我小半岁的朋友,有一段时间聊过很多。内容多因前后个人的变化,而记不太清了,但共享同一页的某种感觉,似乎还存留着。
Losing Young: How to Grieve When Your Life is Just Beginning这本书今年8月出版,出版前就一直在等,出版后听了个有声书开头,其余都是读完。我觉得它比我想做但没有做的事多出了很多。下文主要是内文摘抄。
正午日光下,声音传来,“你之后的人生,会一次次重现第一次的丧失”。这样的总结仿佛对我是新鲜事,但实际上早已实践过。只不过这是第一次有人在我耳边说出来。这样的“判词”简直令人绝望,但确实是早一点得知便能有早一点应对的打算。作者因发现身边没有针对青年人的丧亲互助组织存在,便自己组织了一个,在伦敦的酒吧里聚会。书里采访的一些人便来自于这些聚会参与者。她说在25岁得知母亲再度患病时,她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她引用Grief Works的作者茱莉娅·塞缪尔所讲——“哀伤完全将你抛入一个陌生地景”——“如果你在一屋子人里,她们没和你有共同的经历,你感到不被理解,这让你感觉内心的感受一团糟。你感觉更加生气。如果你在一群五十岁的刚刚丧亲的女性中,你大概会这么想:都不知道你们在哭些什么?你们明明比我多了二三十年。”(虽然这样的想法很无理)这大概也解释了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解释这种可能会发生的思维方式,或者让更多人理解自己和他人。作者得知母亲患病时刚刚硕士毕业,26岁母亲去世前正在德国工作。也是因为母亲临终前建议她去找一个年轻人的丧亲互助组织,她才开始了寻找、创建、写书的旅程。
模仿quarter-life crisis,这里也用了quarter-life grief,从生活、工作、恋爱、友情、婚育等等方面解析不同境况的青年丧亲者的经验和想法。当然面对每一件事,不同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也正是这些差异性的反应恐怕才让读者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原来也在别的地方有所回响,并非毫无参照。
在叙述如今已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许多青年丧亲者的情感体验,以及作者相关体验和反思之外,她也讨论了不同文化背景如何处理丧失,不同社会如何面对这一议题(细节而言,是否有丧假等),互联网是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哀伤的好平台?(许多人可以在这里表达,成为情绪的出口。但茱莉娅·塞缪尔提醒她,往往是那些不表达以及不寻求帮助的人,更处于危险境地。)而她自己在运营The Grief Network,Instagram首页全都是相关哀伤信息时,是否也会觉得需要休息。她花了许多时间鼓励大家谈论哀伤,也分散了她需要与自己的哀伤相处的注意力。(作者也用了一些篇幅写了covid中人们面对丧失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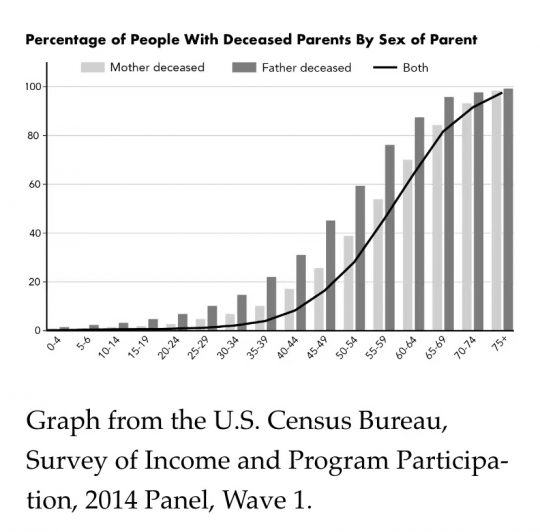
作者对“青年哀伤”有这样大致的定义:“因重要人物逝世引发的哀伤,彻底颠覆了你的假定世界。你对生活的期望——在你所期待的生活中你对那个人的印象——被彻底且无限期地改变了。你以为自己在走的路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岔路口,你正走在一条新的轨道上。这种颠覆发生在你本来就不稳定的生活中:你的身份认同正在流动之中;无论是经济、家庭、社会还是职业上你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于同龄人来说,这种不稳定是一种可以享受、探索和利用的灵活性,而对你来说,成为了焦虑、愤怒或恐惧的根源。哀伤因此成为一种对你的塑造性的经验。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你的决定和你的成年期:你感觉被迫加速成熟,但实际上自己又困在丧失发生的那个年纪,这让人很难完全拥有成人的自我意识。你的身份分支开来:有哀伤之前的你,还有哀伤之后的你。你永远都不可能不知道最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因此大脑会以一种同侪所没有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予以运作。这样一来你感到隔绝:这样的混乱是你的同龄人所不能理解的。随着丧失后的成长与发展,你也许会体验到更强的复原力和洞察力。但这也可能表现为一生中持续的焦虑与恐惧,担心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所爱之人或者自己身上。最终,你需要与它度过余生。”
在后文的故事中,有人在母亲去世的那天仍去参加计划好的新年前夜的聚会。人家问她为什么穿着毛衣就来了没有打扮,她说,因为母亲早上去世了。问她为什么还来。她说不知道。
她说她不愿意被帮助,连这个念头都不愿意有。如果别人尝试,她就推开。
他说他感受到了个人身份的丧失,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扉。“每个人都对我表示抱歉,但我从来都不想成为那个人。”
他们希望去派对能让他们麻木,或者避免面对那些他们觉得会让自己与朋友区分开来的情感。但往往这样的情感是无法被抑制的,总会自然而然找到出口,也往往会更加痛苦。
作者也提到Skins或Fleabag剧中的表现,hot mess这样的刻板印象让人以为“脱轨”就是哀伤的样子。但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并非如此,他们表面上仍继续生活,但内心却已破碎,没办法讲出自己的需要。
另一位丧亲后经常去酷儿俱乐部的人说,有些乐子只是化学作用,十分肤浅,但它们确实是种宽慰。“这是死亡的反义词,不是吗?”它们将麻木带走,让他感到身体的存在。
有些人认为这时候的性颇为危险,因为人本身就处于“失控”的哀伤空间。此外,亲密关系更是困难,因为亲密和连结这样的议题在“丧失”的影响下都会发生变化。一位受访者高中最后一年时男友车祸过世,十几年间,每段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她就要逃。另一位受访者因为丧亲的感受,害怕别人的离开,坚持(在情感上)“自给自足”,没办法建立互相依赖的亲密关系。
对这样的心态当然有很多解释:当你已经因丧亲而哀伤,任何新的丧失(无论是因死亡、心碎还是其他)都会唤起旧的丧失。Dennis Klass在Continuing Bonds中说,“对过去丧失最明显的提示便是一个新的丧失。新鲜的丧失感通常会和别的丧失的悲伤交缠,很有可能对某次丧失的悲伤复现会引发对其他丧失的悲伤。这意味着经历了第一个重大丧失之后,一个人将永远无法摆脱悲伤。”这样一来,开启新关系很困难,同时分手也很困难,因为会带回丧失感。
在哀伤的相互作用上,若丧失发生在家庭中,家庭内部的动态会发生变化。有的人在丧母后会避免谈论自己的哀伤,在旁人提及此事时只是感慨“可怜的爸爸”。作者也描述了一组年轻伙伴们面对共同的友人的离世时,各人心态和哀伤表现的不同。对于哀伤的需要的“竞争”,也会导致其间关系的紧张。
T大学时的男友在上学期间自杀,当时她正好离开学校去别的地方。她无法记起事件发生后的许多细节。她当时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合适的表现悲伤。在她的生活中,她刻意让自己隔绝。她感到自己的“年轻”被夺走了。直到八九年后她仍然感觉这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
对于婚育,作者提到motherless mothering是颇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在丧母之后,女儿便失去了女性身份的某种指引。她们在育儿时会有更强的责任感,也同时有死亡焦虑,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也要经受丧失带来的哀伤。(有受访者说,当自己怀孕时,想到自己是在基因上将一部分过世的母亲重新带回到这个世界上。)结婚、生育都会促使过去的哀伤重现,使之成为新鲜的丧失感,或者说任何转折都会,比如离婚、去职,或者成为祖父母。而哀伤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已经离开没法继续生活的人,他们没办法再有这些经历,也没办法再有这些记忆。
前面曾经提过,青年丧亲者的一部分的自我停留在了丧失之时。因此“早早失去”意味着成人自我意识难以完全建立,导致通常会像某种“冒名顶替综合征”,觉得自己并没有成熟到能完成成年人做的事情。“仿佛是在角色扮演。”“早早失去”意味着成年生活被“失去”与关于“失去”的情感重现所标记,而他人在经历与你相似的人生转折关键事件时,不用感受到悲伤的暗流。实际上,人很难在数月乃至数年内“克服”哀伤,它会随着年纪增长一再触及。
“早早失去”意味着我们在完全做好准备之前成为独立于死者的人。对青年丧失者而言,死亡驱动的焦虑将影响成年期的抉择以及成熟期事件。人很容易将事情“灾难化”。早年失去妹妹的一位受访者说,自己时时刻刻都担心孩子们发生什么事,而自己已经44岁的妻子并不那么想,因为她还从来没有直接经历过丧失。而“死亡驱动的焦虑”对他来说也有益处,因为他感受到了时间的限制和压力,所以需要过好生活、获得成功(还包括生育多子女)。
书里也有一位主人公Claire提起和离世父亲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关系”仍然是可变的。仍有一些她还想解答的问题,但这已经不可能。因为需要另外一方才能形成一份对话,对话意味着对面给出回应。而如果只是一方发起对话,这些感觉无处可去。
前文提到,这本书的采访对象都是生活在不同阶段的“青年丧亲者”。其中一位就是在30年后,等自己的女儿长到自己曾经丧母的年纪时,才开始思考自己的哀伤。(因为丧母时她忙于小家庭无暇顾及自己。)她说,应该“慢慢来”,需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哀伤。
最后一章有关当代哀伤表达(更多的是在互联网世界)。她也提到在动物森友会这样的游戏中,玩家为逝者建立纪念空间,这表明哀伤和纪念的表达实际上是人类本能。(我也建了)
当30岁时,作者就开始计算她距离母亲去世的年纪还有多少年。她觉得这样的压力对于其他30岁的人来说很难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