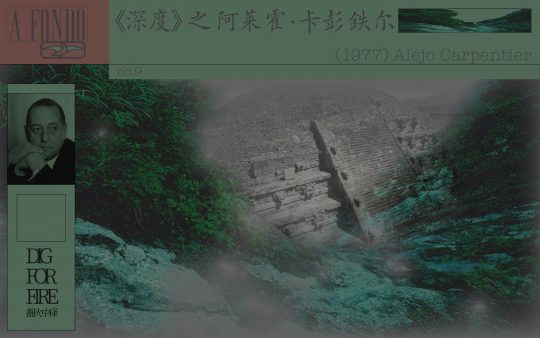掘火中译:《深度》之阿莱霍·卡彭铁尔
译制 | anita
校对 | Joe Oli
后期 | 野次馬
封面 | 可一
片头 | petit
策划 | 掘火字幕组
【译者前言】在着手翻译本期节目之前,我从未听过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声音。这位古巴国宝级作家,讲起话来竟然完全不像古巴人,尤其发不出西语颤音,而是用法语小舌音代替。好在主持人也没有回避谈论他的口音,一开始就点出并给了嘉宾解释的机会,借此引出他的家庭出身。原来卡彭铁尔的法国父亲,坚持在家只跟他讲法语,以自小培养他的双语能力。他说:“我的父亲对我做了一件好事,他给了我两样认识世界及其文化的工具。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他赋予了我这种略显奇特的口音,不像加勒比人,也不像克里奥尔人(criollo)。不过,我自认为是个彻头彻尾的古巴人,并以此为傲。”
本次翻译遭遇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对criollo这个词的解读。作为一个重要关键词和话题,它将在访谈后期再次出现。对criollo[1]最常见的释义是“美洲土生白人”、“出生在美洲的欧洲人/西班牙人”,但这真的准确吗?考虑到其音译“克里奥尔”对于理解词义没有帮助,我本打算在访谈视频中加入注释。结果这条注释越写越长,并且慢慢发现,这个词语在西语美洲漫长的使用历史和丰富的意涵,与本期嘉宾卡彭铁尔的生平与创作有着深刻的关联。所以,我决定把对这个概念的梳理转移到前言之中。透过criollo几百年间的词义演变,我们将看到西语美洲历史进程中,种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作为对这一历史现实的回应,卡彭铁尔的创作主题是如何从非裔古巴文化传统,转向去除种族色彩的美洲主义和世界主义书写。
美国拉美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开拓者、耶鲁大学文学教授何塞·胡安·阿罗姆(José Juan Arrom)曾于1951年专门撰文梳理criollo这个词在西语美洲的意涵演变。[2]该论文虽已年代久远,但因引据丰富扎实,至今仍被视为理解criollo概念的重要参考。阿罗姆索引用的资料时间跨度很广,从十六世纪的殖民时期史料到文章的写作年代,即二十世纪中叶。文中引述的殖民时期资料,多为拉美殖民研究的经典文本,包括西班牙传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的《美洲自然与道德史》(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3], 1590)、印加皇族和西班牙征服者之子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El 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的《印加王室述评》(Comentarios reales de los Incas, 1609)、被视为古巴第一部文学作品的西尔维斯特·德·巴尔博亚(Silvestre de Balboa)的诗集《耐心的镜子》(Espejo de paciencia, 1608)、秘鲁神学家和文学家胡安·德·埃斯皮诺萨·梅德拉诺(Juan de Espinoza Medrano)的《为路易斯·德·贡戈拉辩护》(Apologético en favor de don Luis de Góngora, 1662)、西班牙科学家豪尔赫·胡安(Jorge Juan)与安东尼奥·德·乌略亚(Antonio de Ulloa)合著的《南美洲之行历史记述》(Relación histórica del viaje a la América meridional, 1748),以及西班牙修士伊尼戈·阿瓦德(Iñigo Abbad)的《波多黎各圣胡安·包蒂斯塔岛的地理、民事与政治史》(Historia geográfica, civil y política de la isla de San Juan Bautista de Puerto Rico, 1788)等。
阿罗姆一一摘录和解读了上述资料中出现criollo的段落,并得出结论说,criollo并非是一个种族身份,其特征并不在肤色、血统,而在于“出生在新大陆”这一事实。无论其祖辈来自欧洲还是非洲,只要出生在美洲新大陆(且非原住民),就都被称为criollo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阿罗姆参考的最早文献之一——《印加王室述评》——所提供的一条讯息。作者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写道,criollo这个词是由西非的黑人首创,特指出生在“那边”(allá)、即美洲新大陆的黑人,以与出生在“这边”(acá)、即几内亚的黑人相区分。西班牙人随之也引入了这个称呼,用于将自己和出生在“那边”、即美洲的西班牙人区别开来。由此可见,criollo这个词自诞生之初,就既可以用来指白人,也可以指黑人。其判断依据并非种族,而是出生地。
那为什么“出生在美洲的欧洲白人”、“美洲土生白人”这一类强调criollo种族属性的释义,会在今日流传最广呢?阿罗姆在文中解释,这要归因于发生在19世纪初的一项历史转折,即奴隶贸易的禁止。既然不再有新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出生在原乡的黑人和出生在美洲的黑人之间的对照就渐渐失去意义。又因为仍有源源不断的白人从欧洲各国迁移来美洲,criollo这个称呼便随之慢慢缩小了范围,转而专门用于区分出生在美洲的白人和出生在欧洲的白人。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何在秘鲁学者胡安·德·阿罗纳(Juan de Arona)于《秘鲁俗语词典》(Diccionario de peruanismos, 1883)中将criollo定义为“具有欧洲血统的美洲人”后,这一说法得以广泛流传,并被几乎所有字典沿用至今。在不否认该释义合理性的同时,阿罗姆提醒我们,虽然所有出生在美洲的欧洲人都是克里奥尔人,但克里奥尔人并不必然个个都来自欧洲。
此外,阿罗姆认为,19世纪美洲大陆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和高涨的民族情绪是另一个影响了criollo概念内涵的因素。独立国家在美洲大陆上的纷纷建立,让criollo的内涵从“美洲本地人”具化为阿根廷人、乌拉圭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古巴人等等。为帮助读者理解,我用阿罗姆从19世纪文字资料中搜罗的一些例子作进一步解释。一首智利民谣赞美一位女子,称之为一个“美丽的克里奥尔女人”(esa linda crioyita),这里的“克里奥尔”就指智利本地人。再以秘鲁为例,一位19世纪的秘鲁人曾写:“来了两个智利人和一个克里奥尔人。”根据语境,这里的克里奥尔人应指秘鲁人。阿罗姆还举了人之外的动物和无生命物体的例子。比如,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有一种马,叫做“克里奥尔马”(caballo criollo),这里的“克里奥尔”意思就是“阿根廷的”,因为这种马只存在于阿根廷,在美洲其他地区都见不到。同样,古巴出产一种独特的土豆品种,叫“克里奥尔土豆”(papa criolla),意思即为古巴本地产的土豆;更不用说那道有名的古巴炖菜,克里奥尔阿西亚克(ajiaco criollo),其中的“克里奥尔”即“本地的、本土的,区别于其他国家而本国独有”的意思。Criollo内涵的转变,是顺应独立的现代国家在美洲大陆纷纷建立的结果。至此,虽然它所代表的身份从“美洲人”转变成了个别国家的“国人”,但其基础仍然不是种族,而是地域(国土),其背后的身份认同也不是种族认同,而是超越种族差异的、统一的国家认同。[4]
据此,出生在古巴共和国建立(1902)之初、毕生以身为古巴人为傲的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会在访谈中特意强调要使用criollo这种去除种族色彩的名称来称呼古巴人和美洲人,便是情理之中了。在谈及自己1930、40年代从事的非裔古巴民俗研究时,他说,“非洲根源”或“非裔古巴主义”这些术语“完全不恰当”,因为非洲黑人来到加勒比已经四个世纪,他们早已融入加勒比社会,变成了克里奥尔人。“什么是克里奥尔人?”卡彭铁尔和阿罗姆一样,也引用了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经典论述,说道:“他们既可以指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人的子女,也可以指出生在美洲的黑人的子女,还有出生在美洲的原住民与西班牙人或黑人生的混血子女。也就是说,所有在美洲出生的人,不论来源何处,都是克里奥尔人。”因此,卡彭铁尔认为,不应该用“非裔古巴”这个术语,“讲‘古巴’民俗或‘古巴’音乐才是更正当的”。从“非裔古巴民俗”到“古巴民俗”,抹除的是种族痕迹、种族认同,而目的和归途正是统一的国族认同、对美洲本土的地域认同。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西语美洲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克里奥尔主义小说(novela criollista)的作品,对criollo概念的澄清会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这一类小说的主题特色。克里奥尔主义小说多描写美洲独特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探讨生活在美洲的居民与这片土地上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这批作品的优秀代表,即卡彭铁尔在访谈中提及的三部拉美经典小说:哥伦比亚作家何塞·尤斯塔西奥·里维拉(José Eustasio Rivera)的《漩涡》(1924),阿根廷作家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的《堂塞贡多·松布拉》(1926),和委内瑞拉作家罗穆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的《堂娜·芭芭拉》(1929)。这些小说探讨的人与自然、文明与野蛮、城市与乡村等主题,贯穿了此后的整部拉美文学史。在关于这一批作品的研究资料中,我看到不乏有学者将克里奥尔主义小说和大地小说(novela de la tierra)作为两个含义相通的术语互换使用。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criollo这个概念与大地、土地、本土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
在围绕人与自然这个主题而展开的美洲书写中,我感觉隐隐有一种对环境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的探寻:新大陆独特的气候、植被、地理景观,多大程度上参与塑造乃至决定性影响了美洲人的心理、文化、社会特征?同样是在1951年那篇文章中,为了说明criollo这个概念诞生的必要,阿罗姆参考了西班牙塞维利亚医生胡安·德·卡尔德纳斯(Juan de Cárdenas)的《美洲的神奇问题与秘密》(Problemas y secretos maravillosos de las Indias, 1591),和西班牙诗人贝尔纳多·德·巴尔布埃纳(Bernardo de Valbuena)的《伟大墨西哥》(Grandeza mexicana, 1604)。这些资料反映出当时人的一个普遍信念,即美洲独特的自然环境,必然会使生在美洲、长在美洲的人(无论其祖辈是白人还是黑人、是农场主还是奴隶),在行为与思考方式、语言表达习惯、性情与道德倾向等方面,不同于并非土生土长、而是后来才陆续抵达的外来移民。在巴尔塔萨尔·多兰特斯·德·卡兰萨(Baltasar Dorantes de Carranza)的《新西班牙事务简述》(Sumaria 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Nueva España, 1604)中,阿罗姆继续引述道,美洲克里奥尔人和欧洲人的文化差异,渐渐演变成了矛盾和对抗。随着殖民统治的推进,两群人的冲突将越发激烈与暴力。到十九世纪独立运动时期,“克里奥尔”将成为美洲人反西班牙殖民统治,传达本土身份认同和自豪感的象征。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criollo这个概念的核心要义,就是与地域环境密不可分的“美洲本土性”。原住民、黑人、白人,不同的种族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碰撞、融合;美洲原始文明、非洲文化和西班牙殖民传统之间的杂糅、共生,将美洲变成一片与旧大陆面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不少观点认为美洲criollo精神的实质是种族融合与文化多元,但据我目前的理解,至少从历史脉络上来讲,本土认同才是首要;以杂糅与多元见长的本地混血文化,是依托于这个本土认同而存在着的。对美洲混血文化的宣扬,至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所以能满足独立国家建构初期的意识形态需要,主要原因仍是它有助于培养美洲认同,打造区别于欧洲的本土身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卡彭铁尔在创作生涯后半段转向巴洛克写作,致力于在小说中营造一种感官世界尤其视觉上的繁复,就是为了展现这样一种被他命名为“神奇现实”(lo real maravilloso)的、美洲独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前我会对卡彭铁尔笔下那些时常脱离了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大段景物描写感到不解和厌倦,如《消失的足迹》中的南美洲原始森林景观,《光明世纪》中加勒比群岛上神奇而丰富的动植物形态,《追击》中的哈瓦那老城区街道景观,尤其是各色建筑风格等等。但最近重读后我理解到,将这种写法简单评判为细节的过量堆叠并不公允;奢华繁杂的文字表象下,是对美洲历史、文化与现实的深层思考与回应。语言在他那里不仅是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工具,更是一种拟态(mimesis)——语言本身即为美洲现实的镜像。通过词汇的创造性组合、句法的繁复、叙事节奏的变换,他试图实现对美洲这片巴洛克大陆的再现与模仿(Lambert 2004)。本期访谈中,在解释为何认为“巴洛克风格符合美洲的感知”后,卡彭铁尔向电视观众展示了墨西哥瓦哈卡圣多明各教堂的生命之树图案,以此为例来说明,美洲殖民前的艺术风格如何与征服后西班牙人引入的风格融合,使美洲艺术对色彩和形式的想象变得更加丰富。而他的巴洛克小说,正可以解读为这样一幅视觉图景的文字化成果,由此为美洲的文化身份创造一种贴合的叙述方式。[5]
此外,这种语言不仅是对美洲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被动模仿,也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建构,即以地域认同和混血文化为根基——这也正是criollo概念的内核——打造一种独属于美洲的文化传统和身份意识。在卡彭铁尔这里,根据我的理解,criollo概念、混血文化、巴洛克美学、美洲人认同,所有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的,而隐藏于其中的一个趋势,就是种族视角的淡化乃至消除。被卡彭铁尔视为古巴政治和文学领域先驱与典范的何塞·马蒂,在其发表于1891年的名篇《我们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中,就反对以种族为标准来思考古巴和美洲文化。马蒂认为“不存在种族仇恨,因为不存在种族”,种族只是“病态心理和只会秉烛遐想的思想家们”[6]的杜撰。换句话说,种族分类是人为制造的偏见,因而必须被摒弃。在1893年的《我的种族》(Mi raza)中,他写道:“白人说‘我的种族’是废话,黑人说‘我的种族’也属多余”,以及“超越于白人、混血儿和黑人之上的是人,是古巴人。”[7]马蒂的初衷是反对种族歧视、强调平等和团结,而采用的策略是贬斥种族思维、种族认同。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超越种族隔阂的多元混血文化为基础的、统一而团结的西班牙语美洲。因为摆脱对欧洲文化传统的依赖,同时对抗强大而贪婪的邻国即美国,是他所处时代最迫切的任务。抛开否定种族思维以期实现种族解放的内在矛盾不谈,马蒂的倡议代表着19世纪末最初一代建国者的赤诚理想,而直至1959年古巴革命,卡斯特罗政府宣扬的意识形态也仍然在淡化种族、强化国族,甚至早早宣称种族歧视在古巴已被消除。
在转向巴洛克风格之前,多少受到上世纪前二、三十年世界范围内黑人文化潮流的影响,卡彭铁尔在1930、40年代投身于对非裔古巴民俗的研究,并以加勒比地区尤其海地的黑人传统为素材——他在1977年的《深度》节目中谈及此事,再次将“黑人文化”纠正为“古巴文化”、“克里奥尔文化”——出版了小说《埃古-扬巴-奥!》(1933)、《人间王国》(1949),和音乐史研究专著《古巴音乐》(1946)。然而,《人间王国》之后,黑人题材在他的写作中明显淡化,让步于被他视为更利于描述美洲的文化杂糅现实的巴洛克书写,他的小说主题也更加世界主义、普世化:《消失的足迹》(1953)探讨现代文明下都市人的精神危机;《时间之战》(1956)中借由打通欧洲和美洲两大陆的历史故事来想象一种普遍而恒久的人性;《光明世纪》(1962)的主人公数度漂洋过海,从法国到加勒比再到西班牙,持续追问行动的意义和政治狂热中个体的灵魂归属……可以观察到的趋势是,他以独特的美洲地方文明为起点(加勒比非裔传统、委内瑞拉原始丛林秘密等),来展开对诸如时间、人性、历史等更宏大的普世命题的思考。这份力图在地方和世界、具体和普遍之间搭建桥梁的创作实践,呼应了他引为座右铭的、西班牙98一代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一句话:“我们需要在地方性的深处发现普遍,在局部和有限中发现永恒。”而马蒂在《我们的美洲》、《美洲母亲》等一系列文章中宣扬的美洲主义,实际也具有鲜明的世界主义和普世色彩:“无所不克的仁爱和骚动不息的欲望均属人的共性。各种人体的形态和肤色不尽相同,但其心灵却永远相同。”[8]
时至今日,去种族色彩的国家和美洲身份叙事已经不断遭受批评。意识形态宣传中淡化种族差异,不意味着现实中的种族压迫并不存在。而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黑人群体反过来使用种族认同来对抗国家认同或美洲认同。20世纪的古巴历史、文化和文学,以各种形式见证了不断浮现的来自黑人群体的反抗声音。相比于其他克里奥尔人,他们以被迫的迁徙和离散经历为历史前提的身份认同,与以固定地域及疆界为依托的国家认同无法完全相融(Kaup 2000)。如果我们同意criollo概念的要义即本土地域认同,那么,与奴隶贸易时代跨大西洋漂泊经验无法割裂的黑人认同,和以美洲本土地域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认同之间,也必然存在无法完全弥合的裂缝。卡彭铁尔在本期采访中介绍自己的出身时,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所有优秀的拉美人,要么是土著人生下来的,要么是从船上下来的。”而他就属于从船上下来的那一类。我没能查到那句话的出处,但从欧洲移民的船上下来,和从非洲黑奴的船上下来,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天壤之别。有一个法国建筑师父亲、一个曾在瑞士学医的俄罗斯母亲,并自小接受欧洲人文教育的熏陶(中学即赴巴黎学习音乐,一生有近三十年的时间居住在巴黎)的卡彭铁尔,虽然写作生涯始于对非裔古巴议题的关注,但其个人经验或许注定了,他对黑人群体经验的认同,无法与具有非洲血统的古巴作家,例如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相提并论。纪廉对种族议题和黑人遭遇的不平等有更高的敏感,而在创作领域,也是他而不是卡彭铁尔,将非洲节奏、口述传统和音乐形式(特别是颂乐)成功转化成诗歌语言,从语言形式层面(而不仅仅是主题或题材)在古巴文学中融入了黑人的声音。
在《人间王国》(1949)之后,卡彭铁尔就离开了以非裔主题为主导的创作,但通过这次重读,我在他的后期代表作《光明世纪》(1962)中,再次看到种族视角的短暂浮现。《光明世纪》以埃斯特万、索菲亚和卡洛斯三个哈瓦那年轻人的故事为线索,讲述他们理解和见证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思潮,以及19世纪初的美洲,尤其是加勒比地区的独立运动。维克多·于格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官员,受法国国民公会委派,前往加勒比法属殖民地执行废奴法令。这四人有一个黑人朋友,名字叫奥赫,是个在法国接受了良好教育、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博爱派成员,深受法国大革命“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念和新颁布的废奴法令的鼓舞。然而,该法令在加勒比殖民地推行的过程中,白人奴隶主与反抗的黑人爆发激烈冲突,导致奥赫的弟弟被绞死。愤恨的他面对着与他不同肤色的白人朋友,说:“是你们干的。”这件事让埃斯特万感到,“他们之间产生了冷漠,产生了新的距离,产生了隔阂”。[9]种族对抗色彩更加鲜明地体现于,即便是在废奴法令已经生效之后的美洲殖民地,“黑人已被宣布为自由人,但那些未被强迫征去当兵或当水手的,仍然和过去一样,在工头的鞭子驱使下,从日出劳动到日落。”[10]有一次,为了执行一项维克托派下的任务,埃斯特万乘坐“人民之友”号航行在海上,偶遇一只载满逃亡黑奴的小艇。他目睹了自己船上的军官和水手们如何集体强暴了小艇上的黑人女奴,让“人民之友”名号在现实暴行面前彻底沦为讽刺和谎言。通读小说后会发现,埃斯特万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最接近卡彭铁尔本人。因此,虽然上述涉及黑人的情节在整部小说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但也足以显露出作者对美洲主体叙事掩盖下的种族压迫,仍然保持着清醒。
卡彭铁尔这一代出生于古巴建国(1902年)前后、又适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先锋艺术流派迭起的美洲知识分子(他于20年代参与创立的“少数派”便是古巴当时最重要的先锋派团体),注定不得不面对地方与世界、个人与国族、先锋与传统等多重矛盾。本期《深度》访谈发生在1977年,其中或深或浅涉及的美洲混血文化、巴洛克语言、作家的公共职责等话题,都从侧面体现了卡彭铁尔对上述矛盾的态度。1920、30年代的青年卡彭铁尔,一边追随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的脚步,研究非裔古巴民俗和音乐,一边借由效仿同时代从非洲文化中汲取灵感的欧洲艺术家,进行自己的先锋艺术探索。在1979年写给新版《埃古-扬巴-奥!》(初版于1933年)的序言中,卡彭铁尔回忆那段时光,诚恳地表达了他这一代人面临的困境:“既要做‘民族主义者’,又要做‘先锋派’,这就是问题所在(此句为英文:That’s the question)……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因为所有的民族主义都依赖于对传统的崇拜,而‘先锋派’却必然意味着与传统决裂。”[11]
这也正是文学艺术与现实政治之间最难调和的矛盾所在。前面说过,《光明世纪》这部小说中,有着敏感而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埃斯特万,最接近卡彭铁尔的自我。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在1969年评论集《西语美洲新小说》(La nueva novela hispanoamericana)中,这样评价《光明世纪》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与维克多盲目的坚定相对,埃斯特万代表了批判性的含混(ambigüedad crítica)。”前文所述地方与世界、先锋与传统等矛盾在卡彭铁尔创作中的体现,无一不映照了这份“批判性的含混”。富恩特斯认为,小说中的“含混”具有批判性的力量,因为它释放想象力,维持着对真与假、是与非的开放态度,以此无限接近一个多维度、多重时间性的现实。也正是由于这“批判性的含混”,1960年代的拉美小说得以挣脱传统写实的地域主义(regionalismo)和狭义革命文学的框架,跻身世界文学之林。
卡彭铁尔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在1959年返回古巴前已经基本完成。《光明世纪》正式出版于1962年,但书稿主体已经在委内瑞拉旅居期间(1945-1959)完成。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他重返祖国,投身于革命政府公共事务,担任国家出版社负责人、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之后虽于1966年离开哈瓦那迁至巴黎,但仍是以古巴驻法国文化参赞的公务身份住在欧洲。1977年获得西语文学最高奖项塞万提斯奖后,卡彭铁尔致信菲德尔·卡斯特罗,将该奖项的纪念勋章以及全部奖金寄回,请后者根据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加以使用”。1980年4月去世,他的遗体迅速被运回古巴,葬在哈瓦那哥伦布公墓,卡斯特罗亲自出席了葬礼。在卡彭铁尔的身上,我看到了对于一个当代读者来说,围绕“拉美作家”这个身份标签可以联想到的几乎全部话题,从宽泛而论的文学与国族政治的关系,到更为具体的19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现象与1959年古巴革命的种种渊源(卡彭铁尔被视为文学爆炸的先驱之一)。《光明世纪》为我们留下了卡彭铁尔关于革命政治的最坦诚和复杂的思考。书中被赋予了最高智慧的人物不是维克托,不是埃斯特万,而是索菲亚(人如其名)。关于政治行动,我个人确实也想不到比她在小说结尾的选择更好的答案。(anita)
[1] 西语中的criollo在英、法、葡等语言中都有对应词,不同的历史文化脉络会催生不同的词义演变,这里仅限于在西语美洲这个背景下探讨criollo的含义。另,考虑到“克里奥尔”只是个空洞的音译,再加上想对criollo这个词的中译保留更多灵活处理的空间,因此笔者决定,除去个别地方,本文将在接下来采用其原文写法。
[2] José Juan Arrom, “Criollo: definición y matices de un concepto.” Hispania, vol. 34, no. 2, 1951, pp. 172-176.
[3] Las Indias在本文中将出现三次,我统一意译成“美洲”。Las Indias是西班牙殖民时期对美洲尤其是西属美洲的称呼。这个词来源于哥伦布最初将新大陆错当成了印度的历史误解,但透过16、17世纪的殖民记述、甚至20世纪的资料不难看出,它在接下来的漫长时间里仍被继续使用。不完全排斥出于还原历史语境等考虑,对它进行更加忠实的音译的必要,但本文中暂时先采取意译。
[4] 但其“美洲本土”的内涵也保存了而来,而非被“本国的”含义完全取代。例如,卡彭铁尔在访谈开头说自己“不像加勒比人,也不像克里奥尔人”,根据我的理解,这里的“克里奥尔人”应该是指美洲本地人,对应他的口音让他显得不像是出生在美洲本土的人,而更像外来人这一话题。关于此句中criollo的译法,我在初稿中意译为“美洲本地人”,但出于忠于原文、译法前后一致等考虑,在定稿中改成了音译“克里奥尔人”。此刻重新斟酌,发现内心还是更倾向于意译为“美洲本地人”。我个人认为,对criollo这个词可以保留灵活翻译的空间,除去围绕该概念本身进行的讨论(比如卡彭铁尔向主持人解释“什么叫克里奥尔人”时),或是涉及某些包含这个词汇的固定表达时(这些情况保留其音译“克里奥尔”),其他时候,可以依据对上下文的理解进行适当意译,以便于更明确和高效地传递词语内涵,而不致令读者费解。只要把握住它“美洲大陆或美洲各国本土的、当地的”(且非原住民)这层核心含义,我认为基本不会出太大差错。
[5] 关于这个话题,不能不提的一个人是委内瑞拉文化研究者马里亚诺·皮孔-萨拉斯(Mariano Picón-Salas),他于1944年首创了“美洲巴洛克”概念(Barroco de Indias),用于指代建立在原住民、非洲和欧洲多重文化融合基础上的美洲本土巴洛克,以与西班牙巴洛克相区分。他认为这种独属于美洲的巴洛克美学,表达了美洲在殖民时期慢慢形成的独立于西班牙及欧洲的本土认同(我们可以想象,这里的“本土认同”四字对应的西语正是conciencia criolla),而正是这份身份意识最终导向了19世纪的独立运动。1957年,古巴巴洛克文学代表作家何塞·莱萨马·利马(José Lezama Lima)在评论集《美洲的表达》(La expresión americana)中,进一步将美洲巴洛克称作一种“反征服的艺术”(arte de la contraconquista),再次强调这种艺术形式所承载的美洲主体性及其反殖民内涵。
[6] 《何塞·马蒂诗文选》,毛金里等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7] 《何塞·马蒂诗文选》,毛金里等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27-28页。
[8] 《何塞·马蒂诗文选》,毛金里等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9] 《卡彭铁尔作品集》,刘玉树、贺晓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84页。
[10] 同上。
[11] Obras completas de Alejo Carpentier, vol 1.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Mexico, 1986, p 26.
参考资料(按出版年份)
Fernando Alegría. Historia de la novela hispanoamericana. Ediciones de Andrea, México, 1966.
Klaus Müller-Bergh. “Alejo Carpentier: autor y obra en su época.” Revista iberoamericana 33(63), 1967, pp. 9-43.
Carlos Fuentes. La nueva novela hispanoamericana. Editorial Joaquín Mortiz, Mexico, 1969.
Pedro M. Barreda-Tomás. “Alejo Carpentier: Dos visiones del negro, dos conceptos de la novela.” Hispania, vol.55, no.1, 1972, pp. 34-44.
Roberto González Echevarría. Notas para una cronología de la obra narrativa de Alejo Carpentier, 1944-1954.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4.
Monika Kaup. “‘Our America’ That is Not One: Transnational Black Atlantic Disclosures in Nicolás Guillén and Langston Hughes.” Discourse 22(3), 2000, pp. 87-113.
Gregg Lambert, On the (New) Baroque. The Davies Group, Publishers, Aurora Colorado, 2000.
Anke Birkenmaier. “Alejo Carpentier and Cuba’s Literary Twentieth Centu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ub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321-335.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sXpYzE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