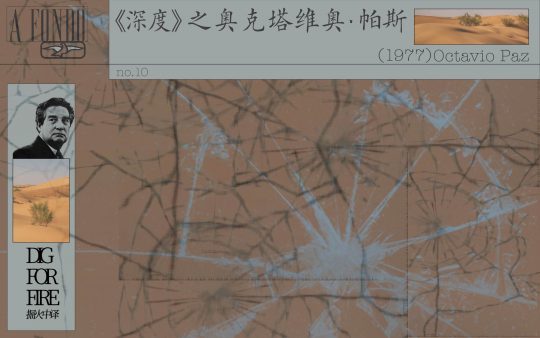掘火中译:《深度》之奥克塔维奥·帕斯
翻译 | Joe
校对 | anita Oli
字幕 | 野次馬
封面 | 可一
片头 | petit
策划 | 掘火字幕组
【译者前言】在校译将要完成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与许多人在帕斯的墓园中合唱,就在这时,从众人的歌声中,我忽然辨别出帕斯的声音——梦中的直觉总是难以解释,因而醒来后,我也深信这一跨越幽冥的合唱。不过倒也无需借用什么精神分析,显然只是访谈听了太久的缘故。
再上一次梦到帕斯则是更多年前,当时的我实际上还未读过多少他的作品,甚至并不会说西班牙语;那时的帕斯对我来说还只是拉美文学史中一座无法绕过却也还未真正注目的纪念碑。梦里,那是阶梯教室里的一堂诗歌讲座,时隔多年,我仍记得帕斯说,“地狱是诗歌无法想象的地方”。(比起那些“排大长队去听帕斯讲座的傻瓜”——波拉尼奥笔下角色语——我早就恬不知耻地插队了!)
未闻其声便听其语,已识其声又闻其歌,我愿意相信,这样的眷顾,是我拾到帕斯遗留的几行轻飘飘的小诗。以这样颇为感性、甚至颇为个人的经历作为前言开篇或许并不合宜,却也能够应照主持人华金·索莱尔在访谈末尾的结束语:“奥克塔维奥之声,奥克塔维奥之语”——《深度》中帕斯的言语和声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起大部分西语者,帕斯说的是一种听起来更为柔和、甚至可以说是更为委婉的西班牙语。因此,或许任何概括或推介都比不上一句“去享受吧”:享受这九十分钟的视听,享受大师如同漫步般娓娓道来的讲述,享受诗人自己的声音朗读自己的作品——如果你也留意到诵读中那些与出版书作中细微的差别,或许会和我一样会心一笑。恰如诗中所写,“这一页诗篇也是一次夜行”,从诗中走过的孩子,正是写下这首诗的人;写下这首诗的人,又一次将其诵读——这穿行于时间中的声音,何尝不是诗的具象,何尝不是一场仍在继续的夜行?
诗歌无疑是帕斯的创作中最重要的体裁。不同的语言即是汇入诗这片海域的支流,时而泾渭分明,亦可水乳交融,于是便有了日本俳句与十四行诗的相遇。作为散文家,帕斯又以同样优美的语言和冷峻清醒的思路,揭开墨西哥人的面具、揭下时间之谜的面纱。
然而走过象岛的湿婆神像、奇琴伊察的玛雅金字塔,却仍需回到被青年的血液所浸染的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即使在今天,帕斯的立场仍弥足珍贵,他的诘问仍切中要害。不妨思考,为何在访谈的五十年后,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主义的痕迹依旧难以磨灭?为何拉丁美洲仍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现象最严重的大陆?为何美墨关系会以更为残酷、更反人权的边境暴力呈现?为何巴以冲突仍在升级,人们仍在大地上流离失所?——“政治本应是共存的艺术”,而现实却常常令人遗憾。帕斯所赞誉的、 一千余年前阿卜杜拉赫曼的所创造的多民族、多信仰共存的神话,已变得像是一枚投向许愿池底、再寻不见的金币。但又正如片头中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还有幸观看这份“文学记忆影像库”,还有幸拥有这来自“世界上最美丽的姓氏——帕斯(Paz)——意为和平”的美好期许。
片头的彩色影像录制于2001年,是为修复版再作的前言,彼时主持人索莱尔已然老去,而帕斯也已辞世;其后的黑白影像,才是最初录制于24年前、1977年的访谈节目。似乎也是巧合,在24年后的今天,再度回看,斯人已逝,我们却仍能继续那场夜行。在此便用帕斯《相同的时间》(“El mismo tiempo”)中的一节,携我们走进那个夜晚、踏入那条河流:
“今天我活着 并不怀旧
夜色流淌
城市流动
我书写在流动的纸张
流逝于词语的流逝
世界并非从我而始
也不应从我而终
我是
一记心跳 在心跳之河当中”
“Hoy estoy vivo y sin nostalgia
la noche fluye
la ciudad fluye
yo escribo sobre la página que fluye
transcurro con las palabras que transcurren
Conmigo no empezó el mundo
no ha de acabar conmigo
Soy
un latido en el río de latidos”
(自译,附西语原文)(Joe)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FZqYD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