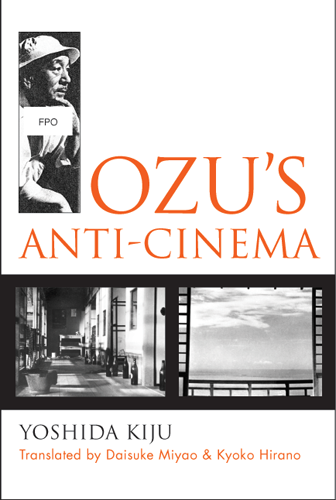小津集成01:代序:《小津的反電影》導言
吉田喜重 著,肥內 譯
兩個難忘的記憶
當我談到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會因為我有兩個關於他的難忘記憶,自然地會喚他小津先生(Ozu-san)。第一個記憶已經是超過三十年前發生的事了,是1963年一月,在鐮倉的一家醫院裡,我和小津先生所屬的松竹大船導演俱樂部在那裡辦了一個新年晚會。由於我經常想起那晚,所以我清晰地記得,彷如昨晚一般。大約十五位導演在場,小津先生是最資深的成員,他坐在房間盡頭的「最高位」,在壁龕旁邊;我呢,則是最資淺的成員,坐在「下位」,在出口旁邊。
當餐宴開始時,小津先生走來坐到我身邊,不說一語地替我倒上清酒,從那時起,直到餐宴結束,小津先生與我喝著清酒卻沒有交流任何一句話。因而,這個新年聚餐,這個按理說應該是很快樂的場合,於我來說就像是一場喪禮。
總之,我非常清楚為何小津先生會做這麼怪的事。前一年秋天,我為一家雜誌寫了一篇關於小津先生最近的一部片《小早川家之秋》的評論,聲稱它感覺不像是小津的片;說《小早川》有些戲有意要迎合年輕觀眾。因為當時我自己很年輕,我能感覺到他的意圖,並且將它指出來。小津先生沒有跟我爭論,反而是為我斟清酒。這是他非常小津式(Ozu-like)的回應。小津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就拿傍晚,小津先生在微醺時不經意地跟我說:「再說,電影導演就像是橋下的娼妓,遮著臉拉客」,這就是典型的充滿戲謔與幽默的小津先生表達法。小津先生很可能,是想隱喻地說電影完全關乎商業;同時,他一定也在問我能否在商業影響之外拍電影。
當然,我不清楚他用這個隱喻的用意為何。也許我不該瞭解它,因為小津先生永遠是用玩笑的方式來談事情,也不希望他的話太被當真。
另一個難忘的回憶,是在深秋的一個濕冷天。我到癌症病房去探病,小津先生那副曾經壯碩的軀體看來如此消瘦。不過,他的意識是清醒的。他對我的探望表達謝意,然後就陷入沈默了。我對於小津先生這麼大的變化,也說不上話來。然後,就在我準備離開時,小津先生向我呢喃:「電影是戲,不是意外。」他就這樣呢喃了兩次,像說給自己聽似的。對我來說,這些是小津先生的遺言了。
一個月後,小津先生於十二月十二日,他六十歲生日當天辭世了。現在,三十年過去了,而我已經到了小津先生過世的年紀了。小津先生從不喜歡說明他真正的想法,他似乎認為這麼做是很輕率的。若我逐字逐句地聽進去,我想他應該會感到很困擾吧,但他在醫院裡對我說的話,經常回來縈繞著我:「電影是戲,不是意外」,當小津先生吐露出這事時,我感到訝異與困惑。我非常羨慕他,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卻仍玩心未泯,且享受著似是而非的表達。
小津先生在他的影片中,盡可能地戒除了戲劇元素,將事件表現得一如是簡單、自發的意外。演員被強烈禁止過度的戲劇性表演,並且也不被允許有特意超出尋常的對話和行為。當小津先生在他臨終之際說的「電影是戲,不是意外」,這話反駁了我們對他的感知,他的電影世界是典型不戲劇化的,那麼到底他的用意是什麼?
我猜想小津先生想說的是,他所描繪的簡單日常事件,就是真正的戲劇,以及,反過來說,其他影片中描繪的故事,則都是人工的與杜撰的事件。然而,儘管我們理解這個,小津先生的遺言,仍在兩個顯著對比概念的前提下,看起來很不尋常。他清楚地落下一句話,卻能分成一個證詞跟一個否定概念:「電影是戲」和「不是意外」。這份清晰與直接,完全與小津先生慣用的輕柔、曖昧以及極為嬉鬧的說話方式不同。
在現實裡,面對他影片缺乏戲劇性的批評,小津先生從不敢直接為自己辯駁;甚至,他寧可簡單地一笑置之,或無視這些批評。會不會是這樣,小津總算是在他面對死亡時,有這麼一次想要表達出他真正感受?
無論如何,他的遺言如此清晰地被分割成證實與否定,以致於必然有另外的意義藏於其中,因而,他的這些話會不時地湧現我腦海裡,令我陷入困惑。
在以上的段落裡,我可能將一些表達方式,如「典型的」、「尋常的」用得太隨意,頻繁地用「典型的小津先生」或「小津式」,製造了一種相同語詞形式的過度重複。然而,我卻不禁要這樣表達,因為小津先生的話,會根據不同聽者而浮游在不同的意義上。在這一刻,某個特定意義躍上了一個人的心頭,但馬上另一個人卻想像出另外的意義。我們會感覺到他文字的偉大廣度與深度。因此,我感覺被困住了,無法決定他到底所指為何。於是我用了「典型小津先生」,而不去拒絕這個概念。不消說,最終在小津影片中是沒有「小津式」的東西,這些作品處在一個意義會不斷地從特定稱謂中,拔錨浮動的世界。
也就是說,讀者在聽到小津先生的電影被以這種反覆、無意義的方式描述,將不會感到奇怪。確實,通過熱情地稱它們為「小津式」,我們欣賞他影像的玩味與深刻,我們享受觀賞他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