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新声(一)I Put a Spell on You

(Robert Palmer)
二零一一年序
1996年8月,我开始在北京《音乐生活报》当记者,和编辑张德甡负责乐海导航版。我们不定期会外出为报社搜集外文原版资料。这本Robert Palmer的Rock & Roll: An Unruly History (Harmony, 1995)便是当时的收获。1997年春天,政策变化导致音乐版面下马,我也就平静地辞了职,在征得张老师同意之后,我带走了这本书,决定将它译为中文。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除了给多家媒体写音乐稿件维持生计之外,精力都投入到翻译中,终于在秋天译完。接下来的几年一直都在艰难地寻找出版渠道,虽然有多位老师帮助策划,勉强绕过版权问题,但还是因为内容而四处碰壁,同时,我也听到评论,说我如此投入精力,应该选一本更好的书——确实,Robert Palmer的名气显然不如Lester Bangs和Greil Marcus诸人出众,而此书又是配合摇滚史电视节目而作,自然在结构和功能上受限。但是,于我而言,在还没有一本系统的中文版摇滚史书的年代,能够读到这么一本书,自然非常激动,而且希望能和人分享——这个思路至今一直贯彻在掘火的运作之中,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更乐意当翻译而不是乐评人。
1999年赴美后希望能和Robert Palmer取得联系,这才了解到他已在我译完此书的那年十一月去世。读到他的另一作品Deep Blues,深深感动,为能翻译他的文字而感到荣幸,并且能感受到两本书之间的通灵。
2001年,此书以《末世新声》为题由百花文艺出版。去年搬家时浏览了出版合同,发现版权早已到期,我可以自由支配这些文字,于是就计划在掘火网刊连载。
当年过的是打地铺吃挂面的穷困生活,不知互联网是何物,翻译全凭一本英汉字典和已有的音乐知识。当时此书中的绝大多数名词在国内都没有译名,很多老唱片无从寻觅,歌词也无法研究,所以难免有很多错讹,如今自己看了都偷偷乐。但因为精力有限,这次的修改仅限于明显的误译,保持原译法并在括号内更正。对于译法笨拙但不影响理解的地方不做修改,保持97版年轻无畏的风格。
真诚期待读者对于翻译细节的批评,并准备随时修正补充。需要我提供相关原文以供探讨的话请提出。
原书按年代顺序分为十三章,另加三个篇幅较长而且内容和多个章节相关的专题,分别位于第二、五、七章之后。这次连载每次一章,唯一例外是本次连载,其内容为第一个专题,之所以将其提前的原因,一是因为该专题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里对音乐进行了研讨,想必会对更多读者有吸引力;二是它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力所在——这本书虽然只有三百多页,但也不是泛泛而谈的作品。
连载保留了英文小标题,因为它们都有典故,如果像当年出版社要求的那样挖空心思译成中文,反而无法传达歌词式的微妙和原出处带着的历史感。
今天为了校对而翻出了一直跟着我原版书,发现里面还夹着TDK空白磁带的标签,算是上一个时代的遗迹。零星的墨迹提醒着我当年消耗的稿纸。虽然书是硬封,还带着完好的dust cover,但也被仔细包了书皮——翻开看,是一张97北京国际爵士节的海报。摇滚乐的精神价值早已在我的生命里完成了历史使命,但作为二十世纪一段关于音乐演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依然精彩。这里提到的某些人名,在我们的后代眼中很可能是巴赫贝多芬一样的神人。
原著/Robert Palmer
译/胡凌云
“如果我们希望发现非洲传统音乐之根,我想我们必须去寻找它们……在传统非洲人对深奥与玄妙的偏好中,在宗教和巫术中寻找。”
——费拉·索旺德(Fela Sowande),尼日利亚音乐学者
“你在你的国家里会和这个家族的成员很靠近。他们了解太多的巫术。我们把他们卖了是因为他们招来了太多麻烦。”
——达荷美乡村的长者,对人类学家麦维利·赫斯柯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 )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祖先把家族成员卖作了奴隶
“这种节奏好象有某种特殊的催眠效果。”
——一位匹兹堡警察,曾在50年代后期的摇滚演出中值勤
“砸碎你的那些鼓吹异教文化和异教生活方式的唱片。”
——明尼阿波利斯天主教青年中心1958年关于摇滚乐的一份通讯
“基督教徒不会参加这场演出。问问你的神父关于丛林音乐的事。”
——1956年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一场“比尔·哈利和彗星”乐队演出场所外的标牌
“那些毁谤我的家伙想给我所做的起个名字。我告诉过人们很多次,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在演奏它。但我确实知道那是什么。它混合着精神的、圣化的节奏和我演奏时融入的情感,我有令人们呼喊的情感。我把它放在了呼喊的模式中,他们就难以抑制了,因为我把它锁定在了那儿。这正是你要干的,如果你不能将他们锁定在其中,他们为会感动。”
——鲍·迪德利,1990
“O my Lord
O my Lord
Well well well
I gotta rock
You gotta rock”
——“奔跑的老耶利米”,约翰和阿兰·洛马克斯于1934年录制于路易斯安娜的传统“呼喊”
(Lionel Hampton)
“旋转的威利,”莱诺·汉普顿(Lionel Hampton)冥思着——他40年代中期的大乐队推出了一种有着重拍子和雁叫式萨克斯的强烈风格,正是后来所谓“节奏布鲁斯”和“摇滚乐”所采纳的——“让我给你说说旋转的威利。”
汉普顿伴着爵士乐、布鲁斯、布吉屋吉和初生的二十世纪一起在芝加哥长大。儿时,他领略了新奥尔良爵士乐的第一批伟人:金·奥利佛(King Oliver)和年轻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他参加了热闹的租场地的聚会(指由房客雇佣音乐家来演奏以赚取房租的传统,最初始于二十年代的纽约哈莱姆,在爵士和布鲁斯音乐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1注,感谢瑜伽熊建议)——在那儿,钢琴家摇滚着布鲁斯和布吉屋吉(boogie woogie——2011注),并且设法不让地主来找麻烦。“我在教堂长大,”他回忆道,“在那里我总想坐在演奏大低音鼓的姐姐身边。我们的教堂有一整支乐队,包括吉它、长号和各种各样的鼓。打低音鼓的姐姐高兴时会站起来在侧廊里跳舞,而我会坐到她的鼓边。嘭!嘭!我一直记得那拍子。那种重拍子是纯洁而圣化的,基督之神的教堂。”(Church of God in Christ,创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孟斐斯,是一个圣灵降临节日的宗派名称,其成员直接与圣灵交流。恍惚习俗——“愉悦起来”,是为他们所广泛传播并鼓励接受的。每一件乐器都被认为是能够歌颂神之赐福的。这种与早期布鲁斯和爵士乐同时发展的圣化福音音乐,是作为摇滚乐起源的最重要也可能是最不文本化的形式之一。)
汉普顿在一支由芝加哥人组织的横笛与鼓的乐队里学习游行乐队的击鼓技法,还从一个赏识他的黑人乐队执导那儿学了音阶与和声。直至1928年他离开芝加哥前往洛杉矶时,已是一个全面的音乐家了。他会打鼓,打击乐和木琴。在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首席爵士乐手合作录音之后,他巧遇白人乐队领班本尼·古德曼并被其雇用。这是个有争议的举动:汉普顿和钢琴手泰迪·威尔逊(Teddy Wilson)是在白人流行乐团中工作的头两位黑人乐手,而古德曼的乐队则是全美最受欢迎的摇摆乐团。不过,汉普顿倒是因此出了名,在4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乐队。最初,乐队演奏的是温和优美的爵士乐和“汀潘胡同”(Tin Pan Alley)风格的流行曲,而布鲁斯、布吉屋吉和神圣的拍子仍未浮出水面——直至他撞见了“旋转的威利”。
“40年代初我在小石城村(应为小石城——2011注)时,”汉普顿回忆道,“我的乐队休息一天。旅馆对面有个剧场,我注意到当晚有个活动,就去看了看。每个人都在奔走相告,‘旋转的威利!旋转的威利今晚要来了。他要让人们在街区排好队,等待治疗。’我决定去看个究竟。”
“我到了现场。‘旋转的威利’的乐队开始表演了。这是支什么样的乐队呵!我先是想把那个小号手拉到我的乐队里,接着又想把他们一块儿全雇了。他们开始摇摆,开始感知圣灵,他们确实找到了愉悦。当然,他们不会跟我走,他们只想演奏主的音乐。我没法说服他们,他们有那种精神和力量。在乐手们渐入佳境之后,一扇后门开了,‘旋转的威利’旋转着进来了,转个不停——从未停下过!乐队闹得更欢了。人们都站了起来,病人们开始试着向前走去——那些坐着轮椅的人。‘旋转的威利’象旋风一样席卷这些人!他抓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把他们从轮椅里扔了出来,朝他们叫着:‘你被治好了!’呜!‘你被治好了!’呜!这些残疾人成堆的落在地上,接着他们站了起来,一脸迷乱的表情,走了。这是我所见过的最震撼心魄的事儿之一。”
“既然我没法挖到他的乐手,我就开始用自己的乐手,让他们演奏那种风格。我想我是第一个把这种音乐从神圣的教堂中带出的人——那种节奏、击掌和叫喊——带到乐队之中。当摇滚乐来临时,他们从我这儿学到了很多。”
42年,汉普顿带领乐队到纽约录制了一首“飞行之家”(Flying Home)(应译为“飞行归家” ——2011注),其中包括一位来自休斯敦、名叫伊利诺斯·杰奎特(Illinois Jacquet)的狂野的年轻次中音萨克斯手。杰奎特让他的乐器尖叫着,重复着同一个音,就象复活之夜神圣执事的祈祷。在现场演出中,杰奎特变本加厉,发出悲悯的吼声,在警报式的高音中会脱去上衣,或是躺在地下炸出粗哑的声音,而乐队其它成员则会冲进人群,在听众脸前吹响他们的管乐,煽动着击掌、扭臀——这时,汉普顿用其生猛的鼓点推波助澜。“爵士乐太冷酷了,我们失去了那些想跳舞的小子们,”汉普顿回忆道,“所以我们开始演奏这种真正挑动性的爵士,人们称之为节奏布鲁斯。”汉普顿给节奏布鲁斯带来名声与(相对的)好运,而“旋转的威利”及其神圣的乐队则消失在神秘之中。
一般地,摇滚乐已被视为两种音乐体系的融合:节奏布鲁斯和乡村西部音乐。莱诺·汉普顿和“旋转的威利”的故事则表现了摇滚乐的另一种血统:它是爵士乐传统的一种延伸。在本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爵士乐是一种艺术和娱乐。在二战前最受欢迎的爵士乐手和乐队领班通常是大众明星——无论那音乐在和声与编配上有多复杂,它总是令人起舞的。但在四十年代中期,——由于战争带来的萧条,也因为美国音乐家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Musicians)的一系列录音禁令和打击——这条大河分流了。其中的一支是为听觉准备的音乐,它迎合更严肃的乐迷,也许就无意中疏离了舞者——这一支变成了“比波普”(Bebop),或称现代爵士。而舞曲的一支,在由以康特·贝西(Count Basie)乐队为典型的西南部乐队将布鲁斯化的硬式“跳跃”音乐传统引入的过程中,变成了节奏布鲁斯,继而又变成了摇滚乐。
和节奏布鲁斯/乡村西部乐理论一样,爵士分支的理论也是简洁而清晰的,在历史上和音乐上都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件事不是因为其本身简单所以就明确了——它引起了一个“与”和“或”的思辨。问题不是摇滚乐究竟是起源于前者抑或后者——所有这些都是它的渊源,而是,象摇滚乐这样一种有着形形色色花样繁多(并且是含糊而难以捉摸)之内容的音乐类型,对其特性的识别是否可以用其它音乐类型来说明。我们的看法是,既然我们自己局限在一种属性的普通比较之中,我们也就只是在说着些术语。而这种音乐的原理是怎样的?怎样的特点用来描述摇滚乐才是独一无二的?这将讨论降低至一个更本源的水平。而在这种音乐中,还有什么会比节奏更为基本呢?
在爵士乐评论界有一条真理,那就是每一次重要的风格创新都始于一种决定性的节奏变换。这在录音技术的拂晓之前就已存在了。那时,早期新奥尔良爵士那复杂的街头拍子节奏开始被拉格泰姆(Ragtime)那种加强的两拍子所影响,接着又被一种更平稳、更重,趋向于每小节四拍的节奏所影响——这被一些新奥尔良元老称为“孟斐斯时代”。(新奥尔良那种滚动的游行乐队节奏与孟斐斯平稳的布鲁斯拍子的相互影响后来演化为第一代摇滚乐的基本节奏动力。)在二十年代后期,大号开始在室内爵士乐团中消失(这和游行乐队正好相反),由更流畅柔和的竖贝司或“弦贝司”所取代。这一节奏部分的变化鼓舞着鼓手们,如康特·贝西乐队的乔·琼斯(Jo Jones),将时值标定功能由贝司鼓转移到钗(应为镲——2011注,感谢瑜伽熊指出)上,这就是被称为“摇摆”(Swing)的爵士乐风格的节奏基础。
在四十年代,现代爵士或称“比波普”发展了一种建立在更微妙、更彻底的切分鼓击节奏之上的旋律语言。“甚至连‘比波普’这个词都是一种节奏形式,”“比波普”创新者迪兹·格莱斯比(Dizzy Gillespie)在70年代中期的一次采访中说,“我总认为每个旋律都有一个特定节奏。你可以给那种节奏润色,但每个旋律都有一种特定的节奏感。现在,当我想向别人示范怎样表演一个乐句,我会说一些诸如‘oop bop she bam’之类的句子,如果他们抓准了音节,那就能奏出这个乐句。”“比波普”标志着爵士乐离开舞池进入听觉俱乐部和音乐厅的起点,这种趋向直接导向了60年代的自由爵士,将音乐从固有的拍子和常规的小节线之循环中“自由”了出来。
摇滚乐在一段不长的时期里,也已经有了一种可以与之相比的演进,从粗暴的舞厅音乐到“严肃”的音乐会。但摇滚乐手们并不认为找一个稳定节拍有什么必要(除了在当代艺术朋克和泰克诺(techno)音乐中)。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的“美国音乐台”节目的人们就有着自己的优先权——当评论新的摇滚唱片时,他们的最高评论是:“它有个好节奏,你能随之起舞。”
摇滚乐的反对者与毁谤者们也早已表白了他们对摇滚节奏的看法。“是那种丛林情调把他们给煽起来的。”一个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官员在该地区56年5月的“骚乱”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不过是一种原始‘通一通’撞击的展示,”在比尔·哈利的“绕时钟摇摆”随电影《黑板丛林》的公演在英国燃起火焰之时,BBC交响乐团的指挥马尔柯姆·萨金特爵士(Sir Malcolm Sargent)轻蔑地说,“摇滚乐,”他补充道,“已经在丛林中演奏了许多世纪。”
纽约《每日新闻》(Daily News)称五十年代摇滚乐为“一种原始丛林节奏套上歌词的倾泻,没有几个成年人想去听。”《天主教太阳》(Catholic Sun)的一个随笔作者称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音乐为“受挫和挑衅的邪教”。如果说对这些关于丛林原始和邪教的言论究竟要引向何方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在权威的《音乐巡礼》(Music Journal)56年的编者按语中已经一览无余:“这种丛林节奏的返祖对他们(青少年)的无法无天有着确凿的影响。它确实将他们卷进了性与暴力的放纵之中(就和这种音乐的狂野偶像们自己一样),而且还成了他们解脱约束,鄙视正常礼仪的借口。”
如何与这种威胁斗争呢?一份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发行的刊物《大新奥尔良市民议会》(Citizen’s Council of Great New Orleans)出台了一个可能会让许多人支持的计划——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明目张胆地表述:
住手
为拯救美国青年
别买黑人唱片
(如果你不想为黑人服务,那就别在点唱机里播放黑人唱片,或是在电台收听黑人音乐。)
这些唱片中怪叫的、愚蠢的言辞和狂野的音乐会在我们美利坚白人青少年心中植下祸根。
打电话给那些播放黑人音乐的电台,
向他们抗议!
别让你的子女购买或收听这些黑人唱片。
很奇怪,这伙(让我们直言不讳)种族主义下流坯们的胡言乱语在一些非洲音乐学者的言辞中得到了回应。比如,尼日利亚音乐学者费拉·索旺德(Fela Sowande)指出,传统的音乐观及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解析性结构主义是显然不同的。对于后者,他写道,“在形式和结构元素上太过关注,却彻底忽视了象征性和心理性元素;将非洲文化构成强制引入西方欧洲音乐构想,比如音阶、调式等等;以及仅以非洲某地区的部分音乐用作‘非洲音乐’这一广阔范畴的描述……如果我们希望发现非洲传统音乐之根,我想我们必须去寻找它们……在传统非洲人对深奥与玄妙的偏好中,在宗教和巫术中寻找。”
在非洲,击鼓能够策动社团议事,同时表达个体与神之关系。一个例子是非洲艺术学者罗伯特·费瑞斯·汤普森(Robert Ferris Thompson)所称的“曲身排列”(Get-down Sequences)。在西非村庄音乐中,舞者曲身成蹲伏状,朝向鼓手,有时以他(或她)的前额触地。这种舞蹈“看似在非洲与表达敬意密切相关,无论是对优秀鼓手其技法的表示,还是对神……曲身包含着致意与忠诚的双重意义。”汤普森认为这种非洲习俗构成了在舞池中“曲身”的非洲——美国(应为美国黑人——2011注)概念的基础,比如“K.C.和阳光乐队”70年的热门曲“今晚曲身?”(Get Down Tonight)。
特定的节奏形式或排列作为精神之力的通道,将人类的个体意识与神联系起来,这一概想对传统非洲宗教和整个美洲中由非洲派生出的宗教来说都是基本的。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音乐中来说,令摇滚乐摇滚起来的基本吉它套路和拨奏,低音走向和鼓的节奏,都能最终回溯至一种原始精神化或祭礼式的非洲音乐。从某种角度来说,摇滚乐是一种“邪教”,它植根于一种与西方文化中自命的卫道士们所信奉的节制、庄重的家长式价值观大相径庭的,充满活力的对自然与精神的欢悦传统。摇滚乐的“丛林节奏”,其丰富和复杂的节奏传统,从特定的非洲文化传播到加勒比(特别是古巴),再到美国南方的黑人教堂,从那儿流进当地舞厅,最后通过录音与传媒,进入大众文化。这一旅程,或过程,是摇滚乐的一个中心演变示例。
莱诺·汉普顿的“旋转的威利”故事,是这种摇滚乐运转过程的优秀示例。旋转运动是来自尼日利亚和达荷美的一种重要的约鲁巴(Yoruba)祭礼的表现;在R.F.汤普森的《非洲动作艺术》(African Art in Motion)一书中被描述为“约鲁巴大地永恒之王的旋转回归”。旋转舞蹈据说始于“一位富有而强硬的神奇国王”,他“转呀转呀转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在到古巴和美国南方的非洲奴隶中,约鲁巴人占相当比例,他们高度发达的城市文化和精妙的宗教与玄学远比其邻近的部落和团体更有影响力。)
更确凿的是,人们能够从约鲁巴到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习俗,到美国南方教堂的“环形呼喊”(Ring Shouts),到“旋转的威利”这样的神化音乐家的“呼喊”(shout)节奏,到节奏布鲁斯、灵歌、方克和希普-霍普(就是后来常说的“嘻哈”,当年翻译之原创可见一斑,您偷着乐就行——2011注)之中跟踪到同样的基本节奏型。在五十年代后期,“呼喊”节奏在一些热门摇滚乐,如“艾斯利兄弟”(Isley Brothers)的“呼喊”(shout)和雷·查理斯(Ray Charles)的“我该说什么”(What’d I Say)之中以一种较纯粹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在录音之前,这些歌是由表演者和听众在创造性的召唤与响应(Call and Response)的集体入迷中在舞台上即兴的。
这种对节奏的精心和群体性的运动远远不止是充当花边,它们将早期节奏布鲁斯、摇滚乐和舞曲与说唱的最新发展连结了起来。而且,一旦我们辨识出了这种特征,那摇滚乐显而易见地不再成为一种美国制造的现象。在牙买加,非洲祭礼节奏也扩散到了城市舞厅,接着进入媒体,在这一过程中生出了“斯卡”(ska)、“稳摇滚”(rock steady)和“雷吉”(reggae)。和其它任何摇滚乐一样,这些牙买加风格也被美国节奏布鲁斯深深影响,而反之也有影响。
举个例子。在六十年代中期,“柯蒂斯·梅菲尔德和诱惑物”的芝加哥灵歌就渗透了牙买加的“稳摇滚”。在几年之内,“稳摇滚”和早期“雷吉”节奏在孟斐斯的南方灵歌之中有明显的体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塔克斯公司(Stax)录音鼓手兼制作人艾尔·杰克逊二世(Al Jackson Jr)的兴趣及其频繁的牙买加度假所致。(“杰克逊会去牙买加或巴哈马群岛呆三、四天,只是为了找一些节奏,”灵歌手艾尔·格林(Al Green)在73年说,“接着他回到录音室坐在鼓边……花好几个小时在那闭着眼打鼓。威利(Willie Mitchell,制作人)会找出艾尔脑中的节奏变化。”)在七十年代后期,DJ库·赫克在纽约南布隆克斯(South Bronx)的集会上推介了牙买加式的DJ说唱,而象“闪光大师和狂暴五人组”(Grandmaster Flash and the Furious Five)这样的纽约人则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说唱和希普-霍普文化。希普-霍普传回牙买加,其影响在“舞厅”风格中得到展示。一切正是这样发展的。
摇滚乐有自己处理传统资源的特定方法(而且所有摇滚乐多多少少都来自于一些更早的传统),这种音乐与其说属于美利坚,不如说属于非洲——美国(应为美国黑人——2011注)人民。在这一切的非洲传统根源之中,音乐绝不简单地是“以艺术为目的之艺术”,它有一种精神方面的维度,一种交流的功能,一种直抵音乐结构之根本以供人享用的定位,最特别的是“召唤与响应”。在传统非洲和摇滚乐中一样,人们从不只是坐着看音乐表演,他们进入其中。他们呼喊。他们曲身。
(Sam Philips)
“别用‘不能’这个词,”山姆·菲利浦斯这位“太阳”公司创始人,摇滚乐之父亲形象正在警告着,他的声音轻微得有些含糊。他坐在深夜孟斐斯城郊家中舒适的椅子里,摇晃着杯中酒,轻轻地对着话筒说着。“我不相信‘不能’这个词,如果你不能帮我接进去,那就转给能够做这件事的人。这儿是山姆·C·菲利浦斯在说话,我要和菲德尔逊(应为菲德尔——2011注)通话。”
这是在60年秋天,给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打电话可不是个好时机。当卡斯特罗以革命推翻了古巴亲黑手党的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并被推为英雄之时,他亦因其马克思主义理想被指责为恶魔。他刚从纽约返回哈瓦纳。在那儿他不顾美国反对,会见了联合国人士。在一片喧哗之中,他带着随员和大量活鸡仔住进了哈莱姆的赛尔莎(Theresa)旅馆。那里常年有着以之为家的黑人爵士乐队、布鲁斯歌者和摇滚乐手。美国媒体为这些“香蕉共和”土佬们和他们的鸡仔大大地热闹了一番。卡斯特罗宣称这些鸡仔是供食用的,因为他处在中央情报局投毒的危险之中——多可笑的偏执啊!从那时起,谋杀国家元首就已成为美国习惯了?
山姆·菲利浦斯也同时被封为英雄和恶魔,这都是因为他放出了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杰瑞·李·刘易斯和他们的摇滚乐手们。后来,埃尔维斯转投更绿的牧场——绿色军营,和来自好莱坞和RCA公司的绿色钞票,而刘易斯则因与未成年人结婚而远走英国。摇滚乐被围困了,而山姆自己也感到被围困了。
菲利浦斯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是百分之百的——至少是百分之百的热血而直率的美国人。但他也常移情于所有那些投奔自己的流浪布鲁斯艺人和山区叛逆者。他常说,美国应该有给“弱小者”的位置——穷人、文盲和没有公民权利的人们。在他看来,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赶跑了一群匪徒,撵走了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权,全是为了诚实的人民,劳动人民;这不正是美利坚正要干的吗?然而美国媒体却给了卡斯特罗一行种种粗鄙的言论——这种处境对山姆来说太不陌生了。
所以,在深夜的孟斐斯,山姆喝了几杯,想了想这事,抓起了电话。第一个接线员告知他现在没法接通哈瓦那,山姆要找他的上司,而上司也无能为力时,他开始按自己的办事方法忙开了——花了一整个晚上,一个又一个接线员,一个又一个国家,但菲利浦斯就是不信“不能”是一个回答。最后,他深沉的声音穿过电缆,跨过六洋,绕地球半周后又折返回来。山姆·菲利浦斯接通了哈瓦那。
山姆被告知,他不可能与菲德尔通话——也许当时他正在讨论那古巴流放者和中情局/黑手党即将在猪湾进行的入侵。山姆仍不愿挂上电话。可能是古巴人不愿让他彻底失望,他们为他接通了罗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菲德尔的兄弟和助手。山姆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了——他也许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并不傻。“罗尔,”他说,“他们在纽约对待你们的态度是不对的。你告诉菲德尔,让他下次来美国时可以来田纳西州的孟斐斯,和山姆·C·菲利浦斯一块呆会儿,也许我们能摆平这件事。”
啊,这巴美关系和摇滚乐政治家风度的金色篇章并不是真如此。这番对话成了一个孟斐斯传奇,仅此而已。但我们可以期待这么一幕景象:山姆和菲德尔,在山姆父亲的城郊私宅就坐,吸着哈瓦那雪茄,饮着古巴朗姆酒,听着山姆的一些“太阳45’”唱片——它们有着黄色的标识和雄鸡啼明的图案——或许那是只小鸡仔?山姆放了一张节奏布鲁斯唱片。“我们古巴有这个,”菲德尔说,“我们称之为‘克拉夫’(Clave),用两根棍子演奏,就象这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在朗姆酒瓶上敲出节奏。“在这儿,”山姆说,“它曾被称为‘火腿骨’(hambone),现在他们管它叫鲍·迪德利节奏。”菲德尔的脸上划过一道迷惑:“鲍·迪德利,他在哈莱姆的塞尔莎旅馆呆过吗?可能我在那遇上过他。他没准也会喜欢小鸡仔?”
让我们先把幻想放一放。任何探究古巴音乐文化和山姆·菲利浦斯所喜爱的中南部音乐之人都会找到两者的许多共通点——在古巴有一定深度的传统中都能找到有关摇滚乐节奏基础的一些讯息。菲利浦斯的成功与其所在的孟斐斯有很大关系——据说,地理上的密西西比三角洲便始于那儿的佩巴弟(Peabody)旅馆门厅,离“太阳”唱片公司的前门不到一英里。从音乐上讲,古巴是美国的密西西比三角洲,是引发当代流行音乐变迁的节奏和音响之源泉:从摇摆到现代爵士、从节奏布鲁斯到摇滚,从灵歌(Soul)直至方克(Funk)。问问古巴人他们的音乐来自何方,大多数人会指向那山多林密的奥伦提(Oriente)省及其首府圣地亚哥·古巴(Santiago de Cuba)——它远在古巴南方,是这个岛屿上非洲宗教与音乐生息的腹地,也是卡斯特罗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说古巴是美国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奥伦提就是古巴的密西西比三角洲。
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音乐、路易斯安娜和密西西比的黑人音乐有着共同的祖先。早在十九世纪,海地革命将该岛的农场主赶走,其中许多人设法带着自己的非洲奴隶一赶逃跑。这些奴隶都是约鲁巴人或芳(Fon)人,来自现今的尼日利亚和达荷美,并有着重要的刚果渊源。许多奴隶最终呆在了古巴,集中在奥伦提省,或是在美国南部,通常是路易斯安娜,也散布到密西西比。这种相同的初始反映在相同的音乐传统中。“在所有的加勒比和拉美地区,”音乐学家莱纳·洛佩兹(Rene Lopez)说,“只有在古巴和美国黑人音乐中,你才能找到在后半拍,‘二’和‘四’拍上的加重,而其它的,从‘加利普索’(calypso)到桑巴,从麦伦圭(merengue)到雷吉,都在‘一’和‘三’拍上加重。”美国音乐对“点子”的重新定位——加重每小节的第一拍,是近期的发展,来源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方克音乐。
固定的低音形式——在古巴称作“图姆包斯”(tumbaos)和美国南方称作“滚石”(rocks)的电报式二至四音符切分句,在古巴的“桑”(son)和美国的节奏布鲁中表现了出来。古巴直至十九世纪末仍在输入非洲奴隶,非洲根源在该国流行音乐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硬核的非洲节奏几乎每天都在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宗教祭礼中响起,在每年春天的狂欢时节则会响彻街头。在十九世纪里,非洲节奏框架走出了奥伦提农村,进入了圣地亚哥·古巴的流行舞厅。在那儿,非洲复合节奏支持着西班牙吉它风格与诗节的形式,伴着非洲韵味的独唱——合唱呼唤与响应。这种新音乐传到了哈瓦那,他们称之为“桑”。当被问到“桑”是何意时,古巴人总是会笑:“它不代表任何意义,”人们坚持道,“它是一种声音。”有次一个古巴音乐家被问及“桑”是不是象“a-wop-bop-a-loo-bop-a-lop-bam-boom”时,“或是象‘比波普’,”他反击道,接着露齿而笑,“是的,真的。”
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哈瓦那已经充斥着“桑”的重低音套路了。这种音乐最有特色的低音节奏型是一种三音符构型,从和声上讲是一个三和弦,类似于五十年代摇滚热门曲劳埃德·普莱斯(Lloyd Price)的(后来是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劳迪·克劳迪小姐”(Lawdy Miss Clawdy)和法兹·多米诺的“乌饭树山”(Blueberry Hill)和“忧郁周一”(Blue Monday)的低音部分。新奥乐良制作人——乐队领班戴夫·巴索罗密奥首次将这种构型(作为一个萨克斯套路)用在了自己的49年唱片《乡下男孩》(Country Boy)中,并使之成为了五十年代摇滚乐大量使用的套路。在法兹·多米诺、小理查德等人的唱片中,巴索罗密奥不仅将这种构型用在弦贝司上,还用在电吉它甚至是次中音萨克斯上,制造了一种很重的底子。他记得第一次听到这种构型是一个低音构型,在一张古巴唱片里。他说那唱片是张“伦巴”(rhumba),但真正的古巴伦巴是另一回事,是一种只有人声和打击乐的非洲流行音乐。随着乔治·拉夫特(George Raft)等人的好莱坞电影引起的美国“伦巴”舞潮,唱片公司也开始在所有拉丁唱片上标上“伦巴”一词,——由“长发教授”(Professor Longhair)和劳埃德·格伦(Lloyd Glenn)推向大众的新奥尔良和墨西哥湾沿岸节奏布鲁斯形式,实际上是个误名。“伦巴——布鲁斯”音乐包含了三音符低音套路(由钢琴家左手演奏)和鲍·迪德利式的“克拉夫”节奏,它不是伦巴,而是“桑”。
在古巴,奥伦提根源转化为哈瓦那流行音乐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节奏上。“切分形式对城市公众的口味来说太复杂,太浓厚了,”约翰·桑托斯(John Santos)在一张二十年代哈瓦那“波洛娜六重奏”(Sexteto Boloña)的专辑中写道:“作为结果,‘桑’的商业化在对非洲节奏与人声的简化中发生了……‘克拉夫’节奏的角色随着‘桑’在哈瓦那流行地位的确立而被提升至重要位置。”桑托斯本也应描述一下这种与美国南方“环形呼喊”相关的复合节奏,而“鲍·迪德利节奏”则是一种美国式的“克拉夫”节奏摸拟。
但在古巴和美国,近年的音乐潮流均有回溯的迹象。自从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及其同道在门十年代中期“让节奏转起来”以来,摇滚乐,特别是方克和希普-霍普,已经更多突破了音乐的欧洲元素——和弦变换、诗性旋律、诗节式歌曲形式,并开始重视人声与打击节奏的相互作用。旋律乐器,如吉它和号角,已经变成了节奏乐器。许多新元素,如转台控制、音响拼贴及各种节奏设备,从基本的鼓机到音序技术,都已经用在了节奏之中。同时,在古巴,由约鲁巴衍生出的“鲁库米”(Lucumi)教派的圣鼓变不仅仅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了。现在,这种沿袭数百年的,标志着约鲁巴诸神的三鼓合声已经可以在爵士乐队和舞厅乐队中听到,甚至在哈瓦那的“热带人”(Tropicana)这样的旅游酒店进行演出。
这些叫“巴塔”(bata)的圣鼓常常三个一组地演奏。它们有三种尺寸,每个鼓有两个不同尺寸的鼓头,使三鼓一组的“巴塔”有一个六音高的旋律范围。其它音高可通过改变鼓头张力获取。约鲁巴宇宙观中的七种基本力量,其各自的存在及其它精神表象都由一种特定的节奏旋律形式表征出来。当鼓三重奏时,这些形式以一种庄严的声音展开,有着赋格般的明晰和复杂的内蕴。在这些形式中,存在着美国黑人用以构造其音乐表达的节奏和弦律。“桑”的克拉夫节奏型,及其鲍·迪德利模拟,都含有大量的“巴塔”节奏,在几个节奏型中就有一个。有些“巴塔”节奏,比如“托奇”(toque),表现的是神圣的“奥娅”(oyá),它以一个反复的三音符节奏为基础,放在美国音乐中就象“汀潘胡同”的热门曲《夜色布鲁斯》(Blues In the Night)的开始句。
“巴塔”鼓手击出“托奇”节奏型,向神之国度发出了信号,邀请或诱使他们下界来“驾驭”或占有他们的“马群”或信徒。有经验的鼓手会关注着人群的情绪,观察着那些“山戈”(Shango)、“奥逊”(Oshun)和“奥瑞莎”(Orisha)的信徒是否有潜入另一种意识的迹象——一种“恍惚”(trance)。鼓手们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击奏,引导某一个舞者进入恍惚,接着又以另一种节奏型将其诱入另一种状态。一些特殊的节奏包含了精确的旋律和节奏设定之外,“托奇”还有一种语义方面的维度。古巴约鲁巴人的祭祀语言“鲁库米”就是一种定音高的语言,每个“托奇”节奏型都有着话语式内容,常常是对神的颂扬和召唤。
必须强调的是,宗教的恍惚祭祀,如古巴的“桑特里亚”(santeria)和海地的“伏都”(voodoo),与催眠术或“心灵控制”毫无关系。这种感应某种特定恍惚节奏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是一种文化氛围强制的行为方式,只有当所有状态“设置”正确时才会发生。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的“贝伯”(bembe)祭祀仪式,其气氛与基督教祭祀是完全不同的。当一些成员进入恍惚时,其它人走动着,小声说着话,或是娱乐性的起舞。“‘贝伯’的完满并不一定在于‘奥瑞莎’驾驭人们,”罗伯特·A·费雷德曼(Robert A. Friedman), 这位曾在布朗克斯的一个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乐团中初练“巴塔”鼓的人类学家写道,“用一个成员的话来说,‘如果他们(指神)不出现也不坏,因为这只是个聚会’。这并不表示一种折衷的宗教信仰;在非洲传统中,“神圣的”与“世俗的”并不相互排斥。
“巴塔”鼓手的原始职能是将人间与“奥瑞莎”世界联系起来,他们通过恍惚体验来引导他人,但自己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根据费雷德曼的记述,他们的“行话”为所有非洲流落他乡者的音乐,包括摇滚乐,提供了一种节奏基础。
由费雷德曼所采访的“巴塔”鼓手将各个鼓的相互影响定义为节奏化——旋律化的“对话”,这是又一种源于非洲的“召唤-响应”。当费雷德曼请他们打出自己在“托奇”中的音响部分时,鼓手们的典型回答是:“我不把它分段,我把它分成对一个完整画面的各种感觉。”在“巴塔”鼓手中,这种画面被称为“律动”(the groove),和摇滚乐中的说法一样。“那种境界,”按费雷德曼及其访者的说法,“是‘音乐的能量变得无所不在,一切都开始动起来’。一个律动是建立在合奏而非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它只有通过真实的演奏才能达到。”换句话说,给予和获取(“对话”)总致力于创造一种联合:律动。相反地,律动只有通过节奏型之间和奏者与听者之间的给予和获取来得到完美强化。
摇滚乐也是由同样的律动所延续的。当我们说一支乐队“摇滚”,那是说他们处在律动之中,已经达到了那种“向前推进的既定方向”之状态(岗泽·舒勒(Gunther Schuller)语),“音乐的能量变得无所不在,一切都动了起来。”在音乐家的俚语中,“摇动屋子”是早在三十年代便在布鲁斯和爵士乐手口中流传的平凡表达,我们注意到,“屋子”其实也是“画面”的组成部分——和乐手们自己一样。摇滚乐作为一种录音传播的音乐,在回馈环节中兜了个圈子。摇滚乐的听众常常看似狂迷的信徒。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吗?这种音乐的基本节奏结构鼓励、甚至是要求一种参与,而在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的“贝伯”仪式中,听者也正是成了律动的一部分。不满的家长和那些自封的特权都不能操纵这一迷人的交流——他们没有“找到”律动,那也不令他们“摇滚”。
为了在祭祀中更完美地工作,“巴塔”鼓都经过了传统的“洗礼”或献祭。这表明,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人化了——被赋予了人的特征。事实上,在整个西非和中非,三鼓组合都是作为一个家庭出现的。最大的巴塔鼓“伊亚”(iya)说着最深沉的语言,是父亲;“伊托泰莱”(itotele),是作为母亲的中型鼓;“奥空考罗”(okonkolo)是最小的、定调最高的鼓,是孩子。这并非简单的民俗或奇想;这种符号主义规定了每只鼓在合奏中的角色。你可以想象,“巴塔”家庭是个高度传统化的家庭。只有最大最沉的“父亲”才有着起始对话、节奏变换和即兴的特权,而演奏它亦是乐团首席鼓手的特权;第二大鼓“母亲”演奏固定的节奏,或在特定的“谈话”或由“父亲”领起的一系列节奏变奏中参加进来;“孩子”鼓太小,还没法加入家庭对话,它在整个“托奇”活动中只演奏重复的、固定的节奏型。
鼓类中的角色分派也在合奏中主掌着推/拉或摇/滚的机理。据费雷德曼说,“每个鼓手必须……对通过掌握自己的演奏速度来制造节奏张力的技术十分灵敏,这叫‘推’和‘拉’节奏,或叫‘在拍子顶端演奏’。‘推’节奏…就是把节奏速度使之比整个脉动听起来快一点儿……‘拉’或‘撤回’是相反的效果,让节奏出现得比整个脉动稍稍滞后一些。‘推’或‘拉’节奏的艺术是指做这些处理而不导致…整体速度波动。”家庭规则表明,“孩子”奥空考罗总是在“推”,象是个积极进取的少年,而“父母”则在“拉”,或是“撤回”,这反映了他们的成熟和智慧。
这些与摇滚乐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听听小理查德或法兹·多米诺的五十年代唱片。——每个器乐部分都分别在推拉着节拍:合奏中定调较高的声音——钢琴家的右手三连音构型、鼓手的击钗在演奏着固定的、竞争性的“推”形式,或是轻轻地冲击着拍子,象是定调较高的“孩童”鼓,而那些较低的常规部分——贝司、低音鼓和嗵嗵(tom-tom)鼓,则在“拉”或“撤回”,象是“父母”鼓。
厄尔·帕尔默,这位在小理查德和法兹·多米诺诸多五十年代金曲中操练的鼓手,在一部教育性录像片《从节奏布鲁斯到方克的新奥尔良击鼓》(New Orleans Drumming From R&B to Funk,由DCI Music Video出版)中,和一支新奥尔良摇滚乐队合作给出了推与拉的鲜明示范。其不同的乐器和套鼓的各部分之推/拉都遵照着“巴塔”的家规。从五十年代便但任录音乐手,并以其七十年代与艾尔·格林的制作工作为人所知的孟斐斯制作人兼乐队领班威利·米切尔(Willie Mitchell),在77年曾富于表现地形容了这种摇滚动力的孟斐斯版本:“我曾留心过这儿的爵士乐手,如乔治·柯曼(George Coleman)和查理斯·劳埃德(Charles Lolyd)。他们演奏得真快,但仍然是保持在拍子后面一点点。那种‘懒散’特征是这个城市中爵乐手和节奏布鲁斯乐手所共通的。即使是比尔·布莱克(Bill Black)的热门曲“烟雾”(Smokie)和“白银沙”(White Silver Sands),或是奥提斯·雷汀(Otis Redding)的唱片,他们总会稍稍地比速度慢一些,而突然每一个会……来一种摇摆。即使是老懒号,——他们总是慢半拍,好象快要掉队了——突然,他们会摇起来,刚好赶上了拍子。在这儿,时间不象个节拍器,它更个人化。耶,号角对贝司说话,贝司对鼓说话,歌手对每个成员说话……依我看,一张唱片就象是人们的一次谈话,向彼此表达自己。
随着方克节奏在七十年代的大众化及后来被吸收进希普-霍普律动中,推-拉和召唤-响应已经越来越深入音乐前沿。而它仍是一种家庭事务:在希普-霍普中,那些定调较高的合成鼓声推着节拍,就象一个太过活泼的孩童,而家长式的低音则在混音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更突出的展现——贝司大师道格·威姆比什(Doug Wimbish,先后参加“闪光大师”、“法兹彗星”(Fats Comet)和“生动色彩”(Living Colour))称之为“击在你脸上的低音”。
通过推与拉来进行紧张和释放,以此构成的持续的、竞争性的节奏型基底是摇滚语汇的中心。在与歌唱、舞蹈等的结伴中,这种节奏运用能有效地将一个听众变成一个入迷的参与者。这种节奏已在宗教祭祀中存在了数百年,从非洲到加勒比,直至美国南方。在美国,奴隶们通常被禁止制鼓和击鼓,他们的手脚以及后来的欧洲乐器不得已地替代了鼓的角色。这一情形随着美国黑人遭遇的一个个紧要关头,给了其音乐一些紧迫感,甚至有一种紧迫感存在于乡下黑人教堂的节奏化音乐和围圈舞蹈之中:呼喊(the shout)。
(Primitive Traits in Religious Revivals)
“那是在一个夜晚,最可怕的景象都展现眼前,这时,营火在先锋们的圈中燃烧着。”这是个老式西方恐怖故事的开头吗?不,这是关于一次1801年基督教营地聚会的记述,地点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顿附近,当时那还是美国的前沿。目击者的描述最初在F.M.达方波特(F.M. Davenport)的《宗教复兴中的原始品质》(Primitive Traits in Religious Revivals)一书中印行,后又被马歇尔·斯特恩斯(Marshall Stearns)那开拓性的根源音乐研究著作《爵士乐的故事》(The Story of Jazz)中重见天日。这个故事记述了一个历史性时刻:新教徒以其热忱组织集会,鼓励黑奴和自由黑人和白人一起做礼拜。其结果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宗教性狂热:“歌曲的形式突破了常规,一次次从人们喉中破碎而出,当一曲完了或是间歇时,那儿充满了狂迷的呼喊、哭泣和呻吟……男人和女人高声呼喊……在一个个牧师间奔跑,好象据说这样会更‘有活力’,热情地云集在一个‘跌倒’的兄弟身边,笑着,跳着,哭着,喊着,神魂颠倒着,晕眩着……有些人象一条出水的活鱼那样躺着,极度痛苦地尖叫着。许多人一连好几个小时地滚来滚去。另一些人狂野地冲过树桩和高地,接着,叫着‘迷失了!迷失了!’冲进森林。”
从这种野营聚会的场面来看,似乎纯粹的“舞蹈”会导致某种激奋。但舞蹈是被《圣经》所排斥的,“邪恶”的举动。而它也是为美国人所认可的非洲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既世俗又宗教。你如何才能说服一个正在跳跃着、迷糊着“迷失了!迷失了!”的崇拜者去停止那糟糕的动作呢?你不能,你该去重新定义舞蹈。在十九世纪初的福音派新教徒来看,起舞是一种承担“双脚划十字”的特殊身体活动。这听起来荒谬可笑,但却可以体味一番。如果你进入恍惚状态,你不会再关注自己双脚的工作。如果你用双脚划十字,那不会有宗教体验——你是在展现一种运动。事实上,输入美国的大量黑人舞蹈风俗被整理成一种节奏歌曲形式,它看似舞蹈,但并未被打上这一烙印。这是“呼喊”,或称“环形呼喊”(ring shout)(和许多传统西非舞蹈一样,它也是按逆时针旋转的环形排列)。它是所有福音音乐、摇滚乐和灵歌的一种原型。
民俗学者约翰和阿兰·洛马克斯(John,Alan Lomax)(约翰和阿兰是父子关系——2011注)于1934年在路易斯安娜乡下录到了一例返祖的“环形呼喊”。它最后以“奔跑的老耶利米”(Run Old Jeremiah)为题制成唱片藏于国会图书馆。它比任何唱片音乐都更加摇滚。“我要摇,你要摇,”路易斯安娜的呼喊者“詹宁斯”(the Jennings)叫嚣着。它和许多宗教词汇一样有着双重含义,即耶酥是救世之石,是一块在危难之时可以依靠的坚岩。(岩石在英语中与“摇”有着相同词形)但呼喊者们也会相互启示着,以一种强有力的节奏摇滚。一个歌者粗声粗气地说出这类简洁的辞句,他的声音是如此动情甚至于摒弃了纯净的声音感觉。一个合唱以无所不在的呼唤——响应形式应和着。乡村教堂的木地板在众人脚踏节奏的强力之下象一面巨大的鼓皮在振颤着,应和着击掌的切分节奏。在许多关于“呼喊”的目击记述中,观察者均指出那脚步声象是在击鼓。它们的职能确实类似击鼓。在于引发并稳定某种恍惚体验。奴隶们发现,种植园房屋和后来他们自己教堂中的木地板,是被禁用了了鼓的唯一有效替代物。地板有着足够的原始振动、有效的响应速度和频响来制造那种触发和保持恍惚体验的大规模律动的兴奋效果。
从洛马克斯兄弟三十年代在路易斯安娜录制的“环形呼喊”录音和八十年代“乡谣路”(Folkways)品牌在佐治亚州录制的《奴隶呼喊之歌》(Slave Shout Songs)听来,似乎与1845年对“呼喊”的首次目击描述没有什么差别。录制后者的阿特·罗森鲍姆(Art Rosenbaum)描述呼喊者为“逆时针方向绕着圈子,带着一种强迫的、蹒跚的滑步,常常曲身或是伸出带手势的手表达所唱歌曲的内容。”阿兰·洛马克斯对路易斯安娜呼喊者的描述则更生动些:“带着一种真实而悠久的西非形式,舞者们一圈又一圈地滑着步子,以逆时针方向移动,用手掌击出复杂的反节拍。教堂的地板构成了鼓皮。歌曲的内容部分是宗教化的,部分是讽刺性的,使用了黑人牧师式的呻吟表达和处于歇斯底里的宗教阵痛中姐妹们的尖叫。”这些记述都表明,“环形呼喊”沿袭了将世俗、讽刺乃至色情内容混合在祭祀之中的西非传统。(在这些传统中,“神圣的”和“世俗的”并非两极分化的范畴,有许多内容落在了它们之间。)由此,我们就有了大量美国黑人福音音乐那种感性的,甚至是色情的意象与情感观念,并且有了一种深深的精神启迪去创造关于爱与性的“世俗”作品,如“烟雾”·罗宾逊(Smokey Robinson)(应译为斯莫齐·罗宾逊——2011注)的“哦宝贝,宝贝”(Ooo Baby Baby)或马文·盖伊(Marvin Gaye)的“让我们干吧”(Let’s Get It On)。
从节奏上分析,“环形呼喊”的行为和那种与吵闹但稳定的跺脚相应的击掌切分节奏有关。随着十九世纪末大量乐器的使用,呼喊者的稳定步伐节奏成了贝司鼓的职能,莱诺·汉普顿称之为“圣化节拍”。呼喊者最具特点之击掌是一种任何鲍·迪德利迷都很耳熟的三拍子重音节奏型。它是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的“克拉夫”节奏/“腿骨”/“鲍·迪德利”节拍的前半部分,一次次地重复。你能在“巴塔”鼓的复合节奏中找到这种三拍子节奏型,它存在于尼日利亚和古巴的各种约鲁巴音乐录音中。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同样的节奏型(及相关变奏)出现在“拉格泰姆”和早期爵士作品的标志性低音部分中。有时它能以一种“呼喊”节奏在活页乐谱上找到(如詹姆斯·P. 约翰逊(James P. Johnson)的钢琴作品“卡罗林娜呼喊”(Carolina Shout))。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它出现在为舞者所写的音乐中。三拍子节奏本身通常被称为“哈巴涅拉”(Habañera),这是个表明其古巴(哈瓦那)渊源的名字。
“呼喊”一词的奇特之处也在于这个词的本义及其引入的过程。早期观察者和当代学者坚持认为“呼喊”特指行动,“它与英语中表示人声表达的那个词只是个巧合。”——罗森鲍姆在其为《奴隶呼喊之歌》所作的手记中写道。换句话说,“呼喊”描述了一种逆时针绕圈的舞蹈,而不是声音的运用。其涵义在摇滚乐的使用中仍得以体现:艾斯利兄弟的热门单曲“呼喊”(Shout)和“纽绞与呼喊”(Twist and Shout)都是关于舞蹈的,并未提及人声的使用:“摇它摇它宝贝/来吧,干起来吧。”
民俗学者们沿着“呼喊”的腹地,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的海岸探究着,找到了一些曾在伊斯兰化的西非学习过读写的忠实家奴的叙述。这些奴隶被委以担任种植园帐目记录的职责。通过阿拉伯奴隶贩运和伊斯兰圣战传到非洲的传统阿拉伯最古老的音乐形式之一,是“索特”(saut),其发音就象“呼喊”(shout)。它有一个深潜的贝司鼓节奏、切分的击掌,还有召唤——响应式的人声互动。另外,“索特”也是一种圣洁的环形舞蹈,它特指麦加朝圣者环绕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神龛“喀巴”(Ka’a ba)的行动——常常是逆时针方向的,这些朝圣者绝不称自己的膜拜举动为舞蹈,而舞蹈在正统伊斯兰教中也和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那儿有同样的“邪恶”意味。
美国黑人的环形呼喊,在那时有一种特定混血来源。它是西非的,或是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的,也有可能起源于阿拉伯;它的宗教相关可能是约鲁巴/鲁库米、基督教,也可能是伊斯兰教。正因如此,它在摇滚乐体系中是一个判例研究,绝非线性而清晰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费拉·索旺德建议我们寻找“非洲传统音乐的根基……在传统非洲人对深奥与玄妙的偏好中,在宗教和巫术中寻找”,这是我们寻找非洲——美国人(应为美国黑人——2011注)的摇滚乐基础时可等同适用的。这些基础是原始精神化的,并非有着“基督教”或“异教”、“教堂”或“礼拜”的宗教气息,而是“有关灵魂与精神的”,“与神圣的事物相关的”,对精神的字典定义。摇滚乐瞄准着自由与超然,将精神性行为化,将性行为精神化,因为这是它生而有之的权利。
(Bo Diddley)
所以,鲍·迪德利,这位将“呼喊”形式引入摇滚的首要人物,在教堂里获得其最早的音乐训练,这似乎完全是恰如其分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第一件乐器是小提琴,而他的老师则在芝加哥南区的“伊本纳泽”(Ebenezer)浸礼会教堂里指导着一支青年管弦乐团。他将自己的古典小提琴技法用在了电吉它上。“我称之为弱音(Muted Sound),”迪德利在94年说,“我从演奏古典小提琴中学到了它……现在他们管它叫方克。”他指的是一种包括吉它制弦的节奏型。这种挥击性的制音节奏吉它能从他的“漂亮玩艺儿”(Pretty Thing)等唱片中听到,这比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新欢”(Brand New Bag),那首由其吉它手吉米·“查克” ·诺朗(Jimmy“Chank” Nolen)和阿尔峰索·“乡村”·凯卢姆(Alphonso“Country”Kellum)演奏的歌曲早了差不多十年。
鲍·迪德利在吉它上的最初影响来自约翰·李·胡克尔(John Lee Hooker),特别是胡克尔的“布吉切尔朗”(Boogie Chille),一支有着圣咏式旋律、没有和弦变化、响着吵闹的电吉它和胡克尔跺脚发出的“呼喊”节奏的硬式摇滚歌曲。胡克尔那夸张的电声、重低音的嗡声和击打性和弦的影响都能在迪德利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但鲍生于密西西比,长在芝加哥,他所受的其它影响是广泛的:从“切斯“公司的另一艺人马弟·沃特斯(Muddy Waters)的乡下电声布鲁斯到凯勃·卡罗韦(Cab Calloway)的西部音乐。
正是凯勃直接影响了鲍在演奏中的快线条表述,并向他演示了任何来自街头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歌曲的主题。卡罗韦在节奏时代的热门曲常常对一些街头风习加以利用,如“游荡者明尼”(Minnie the Moocher)和“吸大麻者”(Reffer Man)。他以此走出了一条新路,只要向其中投入足够的努力,你就能搞出热门歌曲,以街头风格超越娱乐领域。三十年代的卡罗韦与四十年代刘易斯·乔丹(Louis Jordan)都以一支支热门曲开拓着这种作法;到了55年,轮到鲍·迪德利了。他加上了童谣、孩童嬉戏以及大吹大擂的乡下传统和杰罗姆·格林(Jerome Green)的响葫芦(maracas)演奏。那些唱片,有着超前的说唱形式和剧烈翻腾的节奏,包括“发言人”(Say man)(应为“我说伙计”——2011注)、“合上你的嘴”(Hush Your Mouth)、“意味布鲁斯”(Signifying Blues)、和不可避免的“发言人又回来了”(Say Man,Back Again)(应为“我说伙计,又来了”——2011注)。其间,侮辱性的言辞时常显现:“我在某天去找你的女孩/我带她回家……但她如此丑陋/不得不偷偷地喝口水”(应为“我在某天撞见了你的妞。我带她回家…… 但她如此丑陋,她必须得偷个玻璃杯,才能喝口水”——2011注)“噢,我听说你有个工作/是站在诊所门前让人染病!”(这首曲子被认为是第一首rap歌曲, 比The Sugarhill Gang的”Rapper’s Delight” 早了足足二十年——2011年注)
鲍是个不知疲倦的音响实验者。他设计并制作了自己的吉它(包括飞行“V”形、矩形、带尾鳍的和有皮毛的吉它),推广他的功放及其它设备,建造了一系列家庭录音室,并有效地处理自己的许多录音事务。他始终如一地推动着重型吉它放大形式的进程,并以诸如56年“你爱谁?”(Who Do You Love)这样的歌曲成为了一位失真、延音和回授的先驱。他广泛的素材可以来自福音四重奏和“嘟——呜”(doo-wop),比如“迪德利爸爸”(Diddley Daddy)和“迪迪哇迪迪”(Diddy Wah Diddy);或是山区音乐,如“卡迪拉克”(Cadillac)和“跑吧,约瑟芬”(Ride On Josephine)。他在第一代摇滚艺人中占有重要位置,而远不仅止于一个玩手法的人。但他常常为人所的,正是一个手法——“鲍·迪德利节奏”。他与此定义其实并无干系。“那些毁谤我的家伙想给我所做的起个名字,”他在9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许多人说那是‘火腿骨’,我想我一直是个非洲击鼓风格的爱好者,我弹吉它就象击鼓……我只演奏自己的感觉。”
于年轻的鲍·迪德利而言,成长在被称为“小密西西比”的芝加哥南区,找到“鲍·迪德利节奏”应该是环境的体现——它来自于圣灵降临节的沿街教堂,用一块擦皮鞋的布条打出,或是含在人们谈话和步伐的节奏中。正如约翰·李·胡克尔在谈论鲍的至爱“布吉切尔朗”时所说的:“那在他的身体里,终究是要出来的。”而鲍亦坚持自己做了一些创造,而不仅仅是在照搬已经存在的节奏。他们是诚恳而真实的。“鲍·迪德利节奏”的概念并不恰当,毕竟,鲍带来的是一个综合节奏,而他所采撷的传统节奏只是些原始生涩的素材。
象“鲍·迪德利”、“漂亮玩艺儿”、“合上你的嘴”和“发言人”这样以那种节奏构成的录音,与福音风格、“嘟——呜”、布鲁斯、吉它器乐和山区歌曲相比,在迪德利的作品中占了相当比例。在这些作品中,保持一定规则的并不是确定的节奏型或是不同乐器节奏划分的方式,而是节奏放置的方法。通常,鼓手更偏重更深沉的鼓,特别是贝司鼓和嗵嗵鼓,而很少有击钗的节奏型。事实上,许多旧时环形呼喊和击掌的节奏,还有摇滚与爵士击鼓的钗击,都分配给了杰罗姆·格林的响葫芦。这种乐器在混音时常被突出,与鼓有了同等重要的音响位置。鲍的电吉它常常接上一个早期的震音或其它效果装置,照管着两个独立的节奏,分别在低音和高音区。鲍在没有贝司手的情况下演奏了许多年,他将基本的贝司节奏套路在自己的低音弦上奏出,同时,以强有力的高音区拨奏与响葫芦的沙沙声相互编织着。在一些作品中,这种精心的节奏更被响棒(发出古巴“克拉夫”节奏型的木制击打器具)及其它节奏乐器映衬着。有时,钢琴、口琴或是第二吉它会加进这个大杂烩中调调味。在每首曲子中,乐器的布置与平等都各不相同,而整个组合的节奏,或称律动,也是不同的。
从六十年代末詹姆斯·布朗的许多唱片听来,不难辨出鲍·迪德利的音乐指向。其趋势是,每件乐器都变成一件节奏乐器。歌曲间的差异并非从旋律(常常平稳如圣咏)或是和声(已减至一、二个和弦变化,或者根本没有)去分辨,而是从其节奏组织与表述的特性和内容去分辨。按陈旧的“汀潘胡同”模式,——它仍是诸多流行和摇滚歌曲形式的基础和已过时的音乐版权法的基础,一首歌有一个歌词,一个旋律和一系列和弦排列。如果有人写歌用了你先前已有版权的歌曲之词、曲或和弦进行,那么你可以起诉并将胜诉。但你没法以节奏或拍子问题去控告别人——这也是诸如鲍和詹姆斯·布朗这样的节奏创新者没能成为百万富翁的主要原因之一。你能以“鲍·迪德利节奏”或詹姆斯·布朗的方克律动作为核心创作歌曲,而根据法律,你不欠鲍和詹姆斯一个子儿。在这些年,越来越少的艺术家愿去搞创新了。
这种事在音乐史上一直在发生着,而“泰克诺”(Techno)的发展又更将其推向前。现在的数字采样是一种很平常的技术,你无须去模仿一个节奏或律动,你只须从原始录音中取一节来用作自己作品的基础。随着“希普-霍普”的发展,DJ成了音响拼贴师,而说唱乐手则完全是在借来或采样来的声音和鼓机节奏中传达自己的讯息。看来,那些其声音被采样和反复使用的版权所有者要挣大钱了。其实,“采样”并不始于数字技术。“鲍·迪德利节奏”热门曲,诸如约翰尼·奥提斯(Johnny Otis)的“威利与手之合奏”(Willie and the Hand Jive)和“疯狂乡村霍普”(Crazy Country Hop)、巴迪·霍利(Buddy Holly)的(也是后来“滚石”的)“别逝去”(Not Fade Away),甚至是“铁匠”(the Smiths)乐队的八十年代中期热门曲“现在多快了?”(How Soon Is Now)(应为“还能再快点吗?”——2011注),都是鲍作品的采样。不同的是,采样器是人们而非设备。在传统西非文化中,如果某种音乐有着一种有趣的节奏的话,那它就是完美的;简单地说,节奏在非洲音乐中的位置正如和声在欧洲传统音乐中、旋律在印度音乐中的位置同样至关重要。印度音乐众所周知是没有和声的,而许多欧洲古典音乐在节奏方面是单维的——可以说是很原始。但是,当流行音乐开始脱离“汀潘胡同”模式和价值观,拥抱其原始的非洲渊源时,突然,我们的新文化被视为脱节的、不知所措的、被损害的、颓废的和腐朽的。有一些老家伙著书哀叹着“美国流行音乐美丽与内涵的沦丧”,而其它人则攻击重金属、朋克或说唱——无论最新的流行音乐怪物是什么,它总是在危害着文明的丝丝缕缕!(“其它人则狂野地冲进树桩和高地,接着,叫喊着‘迷失了!迷失了!’冲进森林。”)
如果这些嘀嘀咕咕的流言蜚语散播者能发现这种音乐的历史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其本身则是从自身源泉中汲取营养周期性更新自己的语汇的话,这对他们是有教育意义的。摇滚乐最早的美国先导,比如“呼喊”和劳作歌曲,就加重声音与节奏——一个拍子就是一个讯息。这其中部分源于非洲传统,部分则是一种需要——人声和跺脚声常常是可以使用的唯一音乐表达。在黑人解放后,乐器拿到了手,黑人文化的音乐语汇也就令人惊叹地绽放了。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和二十世纪的头一、二十年,一种史无前例的音乐热潮展开了:拉格泰姆、布鲁斯、爵士、福音。在二战期间及其后,一种相似的,甚至是更明了的热潮再度袭来:比波普——一种摇摆时代的舞曲基础爵士乐;非洲——古巴(应为古巴非洲后裔——2011注)爵士和萨尔沙(Salsa)——将古巴“桑”的简明低音构型与单和弦即席伴奏带进了美国音乐主流;还有大量的节奏布鲁斯变种,从爵士化的乐队布鲁斯到布吉屋吉到乡下电声布鲁斯到不同的流行和福音人声团体。这些种类和亚种类(它们在实际上已经重迭)已经在周期性地汲取本源。而根源与提炼的融合形成了一新形式,在年轻人听来是新鲜而奇特的。
白人音乐家很早就创造出了他们自己的音乐语汇;白人制作人对其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修饰;白人包装者则将音乐送至全球。但有一个事实是铁定的,那就是音乐的源泉,其关键的美学规则,它的基本结构,是传统非洲和非洲——美国(应为美国黑人——2011注)的。精神与节奏、讯息与节拍,是这种音乐的主导规则。在某个特定的情感温度上,他们熔化了:节奏精神化了,而精神有了一个你能随之起舞的节拍。让你想要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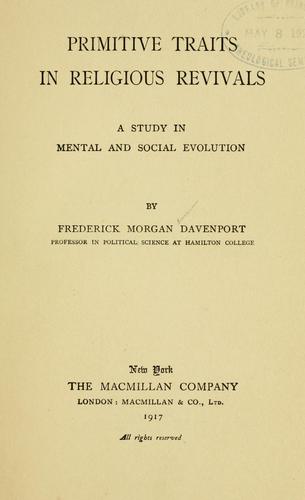

[…] 介绍及连载一见:https://www.digforfire.net/?p=3391 […]
非洲——古巴、非洲——美国分别译作非裔古巴人与非裔美国人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