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遊2009年(PART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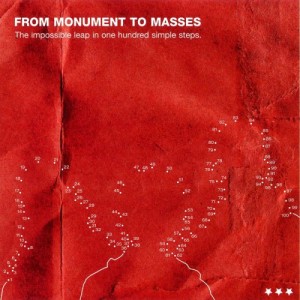 文/肥内
文/肥内
2.寻找材料
加入豆瓣一年多之后,在那里也认识了很多人,这让我在拓展,或者说,推销自己文字的范围在今年里宽广了不少。当然,相对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中断某些原有的园地,像是本来固定替台湾的国家图书馆《新书快讯》写的书评,今年可以说完全停产,用「可以说」是因为写过一篇不满意而没交出去,以及构思过另一篇,但由于书本身太难,我无法完全掌握,所以放弃。新开拓的园地,有些诉求通俗倾向,有些要求创意,再加上论文开题的需求,这让我不得不看一些影片来寻求灵感。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算真正找到适合于论文或者写文章用的题材,反而找到了一些像戈达尔(Jean-Luc Godard)一样不断开发电影材料可能性的创作者,其中两个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导演古兰(José Luis Guerín,天知道这个导演的名字要怎么发音,随便叫一下好了…)以及捷克新电影导演希蒂诺娃(Věra Chytilová)。
古兰的《在希尔维住的城镇上》(En la ciudad de Sylvia,2007)首先映入我眼帘。这部片基本上是一部没有情节的影片,但这点并非吸引我的主因,不过也足够吸引我了,就像在马里昂巴被构筑的迷宫一样,男主角几年前与希尔维相遇过的这个小城,也是一个迷宫,一个阻碍他寻人的小城。房内写笔记、露天咖啡厅听人们说话、穿街越巷地跟随、轨车上的搭讪、站牌边的等待,大致构成了这部影片的全部。但有趣的是我们从音轨上听到的声音。这些声音有指向性,但不属于被摄物,而属于拍摄物——摄影机。简单来说,这部片主要的实验,就是「听点」的游戏,但当然它做的还不够彻底,若要依据摄影机听点来看那一长段咖啡厅的戏,或许会有些迷惑。总之,一如古兰10年前在的作品《影迹》(Tren de sombras,1998),这部顾名思义实验关于「影子」的影片,首先追踪了一段老旧的胶片,不过跟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作法不同,古兰这部「非剧情」片里头没有具体的人物与人物行动,一切只有现象,或者说,一切只有影子,包括记录在胶片上的影像,也只是纯粹的影「迹」:一切可见仅是光与影的作用。创作模式接近,当然问题也一致,就是长达一部标准长片长度的实验片终将招致的沈闷与冗长它们也是避不了的。想一想便知道,影史上并没有几个人能像雷奈(Alain Resnais)。
在希尔维呆的那个城市里,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透过静止的摄影机,悠闲地遍览风光。而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让我悸动了。就在男主角于公车站紧盯的女子身上,光影就这样在她身上来来去去。莫内(Monet)的鲁昂教堂,现在闪现在这位女子身上,美得不得了。这与小津在《独生子》(一人息子,1936)中设计的那一分多钟的长镜头不尽相同,虽然小津透过声音,将母亲、妻子哭声转为隔壁邻居小孩的笑声,在「技巧」上更加惊人,多年后,潘(Arthur Penn)在《小巨人》(The Little Big Man,1970)的音画蒙太奇用上这一技巧时依旧很有效果,古兰捕捉的是时间,是影像内在的绵延,是镜头内部的正反打,情绪完全由影像决定。这个镜头除了先与小津镜头比对之外,还让我想到徐浩峰在课堂上谈到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樱桃的滋味》(Ta’m e guilass,1997)中一段从大远景拍摄男主角所驾的车蛇行于山丘的蜿蜒道路时,指出在云遮掩阳光的情况下,路途中忽名忽暗的车影,基本上就是一种正反打,内部正反打,这也是我刚刚会提到镜头内部正反打的概念,这是从徐老师身上学到的,不敢掠美。第三个令我想到的影像,是七月份回台湾后,找出是枝裕和的首部作品《幻之光》(幻の光,1995)中,一个在市集上的镜头,远景,男女主角在市集的一角挑菜,与菜商谈话,内容无关紧要,但这个阴暗角落突然在天公的开眉中,突然一片光明夺目,那是主人公在探求的一种平静生活的肯定,而这是电影的特殊符码。
不过古兰要当心,因为这种创作模式,很可能会把他自己掐到死胡同,就像我现在一边听着今年大热门专辑——The Animal Collective的《Merriweather Post Pavilion》——的感受一样(这张专辑一听就知道肯定要被西方媒体评作21世纪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或《Pet Sound》),即便这种无所事事但却对材料诸多开发的作品,也是我自己梦寐以求的。
古兰的影片是让「影片本身」无所事事,希蒂诺娃的作品《雏菊》(Sedmikrásky,1966)首先就是先让两位同名的女孩无所事事。透过无所事事,以极端的人工化,嘲讽这两位女孩想「转大人」所进行的各种冒险。人工化体现在她的蒙太奇,她炫丽的色彩,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材料呈现,好比戈达尔在许多他60年代的作品那样。
关于希蒂诺娃我现在还没有太多话可以说,因为怕说的不够精准,不能随便谈,再说,在关于她首部长片《关于某事》(O necem jinem,1963)的简短心得中,我已经说过一些粗浅的看法,对于她蒙太奇特征的关切,早在希维特(Jacques Rivette)等人在一篇名为「蒙太奇」的文章中已经提醒我们了。但在起初,希蒂诺娃的蒙太奇更多是一种平行设计的方案,这与第二部作品(《雏菊》)的攻击性不同,她在这里的挑衅成分,除了面向观众之外,它也挑战电检,所以它一完成便被禁也是意料中事。
希蒂诺娃的实验持续着,在她被完全禁止拍片之前,她还留下一部非常有趣的《乐园禁果》(Ovoce stromu rajských jíme,1969)。在这里,韦尔斯(Orson Welles)式的广角镜头被她义无反顾地突出了,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式的色彩迭合也被几乎没有限度的使用,让这部取材自圣经中亚当与夏娃故事的影片,变成一部灿烂的调色盘。东欧在60年代大行其道的动画风格,也在本片中透过人物肢体表演,甚至是抽格的手法移植进来。
可惜的是,在被禁拍八年之后,从《禁果游戏》(Hra o jablko,1978)开始,她的作品在形式的处理上收敛不少,这部完全是关于一对夫妻生活上遇到现实问题的婚姻片,总算能以真挚的情感感动我;但在《灾难》(Kalamita,1982)中,她笔下那位太过冒失的主人公则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他所到之处造成的混乱丝毫没有幽默感,至少是对我来说,这让影片演不到一半就令我昏昏欲睡了。处理冒失天使仍是达地(Jacques Tati)及其徒子徒孙(见本文的第一篇连载)的独门秘方。
基于对考克多(Jean Cocteau)《双头鹰》(L’aigle à deux têtes,1948)的好感,加上总算找到英文字幕,暑假在家将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欧布瓦的秘密》(Il Mistero di Oberwald,1981)看完。后者作为前者的翻拍,在故事上并没有太多的更动,再说,从他才拍完奇片《职业:记者》(Professione: reporter,1975)的题材看来,翻拍考克多这部颇有寓言味道,谈一对长得完全一样,但身份与命运完全相反的人,让一女子先后爱上的故事,也可以说只是迟早的事。可惜考克多那一部由于太过煽情的配乐,以及糟糕的翻译,使得我在欣赏上,有一定的障碍,但却仍不能阻止它成为我的年度榜首,算起来,也是为了过去我过于低估考克多的一次补偿,否则,今年在撰写论文的需求下,我多看了好几部伟人欧弗斯(Max Ophuls)的作品,要占据我的年度观影榜,基本上看到的都会是导演栏为MO的作品。考克多的柔情,在削弱不少的实验性后,体现出一种异常柔美的气质,就好像希维特六年前那部可以说达到《牡丹亭》境界的奇情片《玛西与朱利安》(Histoire de Marie et Julien,2003)那般。
回到正题。安东尼奥尼这部电视片,或者说「录像片」,有一处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两三个空景中,多是拍摄草地,他透过调光装置(不确定是附在摄影机上的还是后期调整的)让色彩的变化,直接保留在画面上。他透过这个调色的过程,是想向观众传达什么吗?是不是想贴近女主角——死了丈夫的王后,爱上了前来刺杀她却和先夫长得一模一样的刺客——的心境吗?根据一则访谈,导演自己称说这个新媒体给他许多的乐趣(这种乐趣显然不同于它所带给雷诺阿〔Jean Renoir〕、韦尔斯或戈达尔的),可能这个调色效果也是乐趣之一吧,不得而知。
虽然不知道安东尼奥尼的用意何在,却让我想起暑假发生的一个事件,我称之为「《不能没有你》事件」。熟悉本网刊的豆瓣马甲的读者,可能对这个事件有点印象,胡总编曾将我与网友对于这部台湾片的讨论转贴在豆瓣马甲中(忘记的人可以前往这里唤起回忆: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728275/)。在那个事件中,我与网友主要因为这部黑白片之所以呈现黑白有过一小段争论。为何会争论?对我来说,这部影片的「颜色」问题从没有曜进我脑海里,但网友们却对这个问题大发议论。其中有网友更引用导演的说法:「因为找不到适合本片的颜色而选择黑白」(大意)。于是这让我想起安导,他的调色,是否在找寻适合影片的颜色?我们还看到《欧布瓦的秘密》将一位大臣上色,或者说「抹色」,使他呈现一种单色(偏黄,有点像默片时候专用来拍内景的色调),把他跟其它人区分开来,他在片中一度试图要阻止刺客与王后的结合。我会这样想是因为这让我思考「到底什么题材是适合什么颜色的?」这样的问题,对于题材与颜色之间的关系,难道有绝对的吗?这种感觉会不会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两年前,法国一部类似的影片《谷子与鲻鱼》(La graine et le mulet,2007)为何是彩色片,而我们也不觉得影片里头有任何足以令我们产生偏见的颜色啊。再说,根据参与创作的工作人员私下表示,《不能没有你》之所以呈现黑白,是因为拍摄时虽以彩色拍摄,但技术太差,以致于过带时发现颜色都不接,考虑到连戏问题,最后才退而求其次地过成黑白片,这么一来,导演的声明不就是一种漂亮的谎话吗?事实上,这无论如何都得说是主创人员的能力不足,否则,让我们看看韦尔斯与巴赞(André Bazin)的访谈就知道,他断断续续拍了四年的《奥塞罗》(Othello,1952)也因为用上了各种不同的胶片使得剪接工作异常辛苦,可是,若没有他本人的说明,观众根本看不出来它用了几种不同的胶片拍摄,更不用说每个主要角色其实都是三四个不同人演出的!
深层地想起来,网友们对《不能没有你》的论述,还在于某些非理性的介入,这让讨论无法确中核心。可是这种问题何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对于美国导演葛瑞(James Gray)的喜爱,起源于去年初看了他的《杀手悲歌》(Little Odessa,1994,直译是「小敖德萨区」),那是因为网友极力推荐他两年前的作品《万恶夜总会》(We Own the Nights,2007)的缘故。而我对《杀》与《万》也确实都有好感。因而去年后半年紧接着又看了葛瑞的第二部作品《家族情仇》(The Yards,1999),也相当不俗。今年则是望穿秋水看到了葛瑞去年的新片《两个情人》(Two Lovers,2008),在某种「好感贺尔蒙」作祟的情况下,对它依旧有高度的好感和平价。这让我在九月时有机会为台湾的《电影欣赏》杂志写一篇关于葛瑞的专文。为此我重新看葛瑞截至目前为止拍过的这四部作品。有一种疑惑却不断地浮现。
我发现他的这篇专文非常难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没有优点,而是没有「特点」。他的一切优点,就像许多好莱坞优质导演一样,都是来自一个大传统下的优点。纵然葛瑞的血脉主要是从60、70年代的新好莱坞开始的。但毕竟还是一种传承。
不过,尽管我自己仍有一些迟疑,规模很小的《两个情人》不管怎样也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在老套中肯定了基本功的重要性,作为独立作品,无疑也是有鼓舞作用。比起有许多东西要讲,但却讲得很乱的作品,无疑我会偏爱这种虽小但很严密的小品。
到头来,欣赏艺术品,虽必须具备基本的鉴赏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学理论),不过非理性的「动情」(pathos,德勒兹语,台版翻译者这么翻的)似乎也不可免。
不过,在这个找寻题材的过程中,在实质收获上,大概是苦乐参半吧。论文开题虽然通过,但我当然知道答辩老师对我的题目是抱着保留态度,而我自己确实也没表现好;论文的写作到目前为止,仍处于难产的阶段。而对于主流媒体,则相当缘浅。经朋友介绍,我开始等待《看电影》跟我联系写关于新浪潮的文章,但直到今天,我还在等这个消息;《环球银幕》则退了我好几次稿子,从去年的《欢迎来北方》(Bienvenue chez les Ch’tis,2008)、《海角七号》(2008,关于这部片我写的那一千多字的文章,后来被撷取了两三百字,聊备一格地被刊登出来)到今年的郎(Fritz Lang);而电影时光网(Mtime)则回绝了我一篇其实应该会蛮有趣的新浪潮回顾文章,而原本规划写的一篇「值得观赏的百部佳片」项目也流产了。其实这个文章世界仍是不容易打进的领域,我在几年前为台湾的雅虎音乐网写的乐评也被本刊编辑拒绝过,或许这也是为何我对写音乐文章非常畏惧的原因之一吧。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