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旧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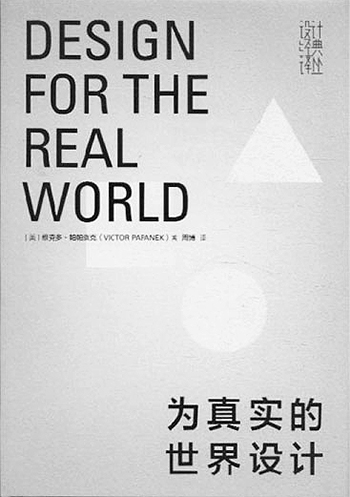
“创造的个体以一种十分自我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们以牺牲观众或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这股风潮像癌细胞一样从艺术开始,迅速波及大多数的手工艺门类,最终也影响到了设计。”
文/petit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平面设计还是工业设计,哗众取宠(设计界的术语是:创意)似乎是最先被人们了解和(作为一种默认的职业素质)接受的。那些有着毫无意义线条的海报、夸张的画册开本、一点儿也没有“请吃饭”含义的餐桌和坐起来极不舒适的椅子构成了我们这个视觉华丽的世界。设计师们对风格的追求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探索,演变成另一种“设计”身份认同。然而事实上,所谓的风格多样化其实和设计需求没有多大关系,它更像是一种消费需求。
某种莫名的自我感觉良好使得设计师们认为设计足够改变世界——呃⋯⋯可能没这么厉害,但至少也能保持持久价值,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34年曾选定了397件被认为具有“持久价值”的设计,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有396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剩下的那个是烧杯),而更多的例子存在于20、30、50、70、8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设计师们急切地想要改变世界,他们为“未来”做设计,并期望通过这种前瞻性来彰显自己的传奇色彩,大师谁都想当,未来的人们会自动忽略你做过的那些猥琐拙劣的设计并紧盯着你的代表作,坚定地认为此人这一辈子都在为真实世界的美好而奋斗着。
假如说对“未来”的热衷等于是对“现在”的不满,那也多少可以让人理解。但问题之一就是“新”的东西常常包含着试验(自然也包含着试验的失败),然而现实世界则是以成功为导向的文化体系,对失败的容忍程度很低,这也就意味着设计师既要负责开拓也要负责失败之后的责任。此种环境催生出许多“成熟”的设计公司和跨国设计事务所,其作品饱含着老道、世故和油腔滑调的设计伎俩。
所有这些最终将设计师导向了一个趋势与行业规则:即美好世界的定义是由设计师作出的,而凡是不美的区域都可以被歧视。贫困地区、第三世界、基础设施、政治权利和人权被剥夺的地区、病、老及残障群体,他们的世界显然都不包括在内。也就是说,真正的真实世界仍然在设计师们的臆想之外艰难的存在着,我们所谓的“设计师责任”其实本身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虚假概念。
在维克多看来,就算是经典的设计,也可能因为新时代所产生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观念而变得可以持续改进。然而,也正是这种设计思路过于精密和细致,它所包含的设计价值过于宏大,设计必须展示除了美学和功能之外的更高价值,即:设计是一种人类对自我世界的持续进化。而这种观点被高度消费主义的商业世界视为“反常规”的乌托邦幻想。
这就产生了一个怪异的现象,设计师们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维克多也认为设计可以改变世界。但世界并没有被很彻底地改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设计师们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尝试着改变世界,而真实的世界则被所有人忽略掉了。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最原初的责任可能就是来自设计教育的缺陷:关于设计学校的弊端似乎就是专业技能教太多了,从而忽视了那些和设计密切相关的思潮,例如社会、环境、经济和不断变幻的流行文化。而正是技术主义导致了设计师逐渐成为了外观装饰家和大众称为“美工”的那类专门技术员。
而且,即使是技能,现如今的设计学校也都走在一条保守中庸的路线上。包豪斯、构成和瑞士国际主义风格之类的。甚至学生们也被要求从事手工制作,海报、版画、丝网印刷⋯⋯诸如此类,完全忘记了2000年之后是触摸屏和在线数据处理的新时代。这是 CSS 、Html5 、和动态交互程序的时代,学习使用圆规和锤子对这个时代的设计师来说毫无意义。
维克多说道:“⋯⋯学习必须是一种狂热的体验⋯⋯因为学习就是改变。教育就是一个程序,其中,环境改变了学习者,而学习者也改变了环境。”这就是所谓的完整的设计(integrated design),意即设计师不应该过分追求设计技巧的深度,而应该注重设计内涵(与设计责任)的广度,毕竟,设计作品是要与人沟通并且与当下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如今,维克多在 70’s 所阐述的这些关于设计责任的问题很多已经在新千年得到解决,他把很多设计师无法企及的公共政策和所能支配资源都归结为设计责任的激进态度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解决。尽管来说旧世界的很多问题被解决了,但新问题仍旧层出不穷。每一代设计师都面临着每一代的新问题,每一代设计师面临的新问题仍旧需要激进的观点去提示以便改进,在此意义上,维克多的态度仍旧具有参考价值,即便在学界来说,他描述的是一个“不真实”的真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