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与北岛
八月的最后一天,下午北京大雨,我在积水潭附近西海畔的一个小院内避雨,读北岛《蓝房子》。<波兰来客>一篇提及“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学同学唐晓峰神秘地告诉我,他的邻居是地下艺术团体‘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这两个称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北岛,《蓝房子》,凤凰出版传媒,82)看到唐晓峰三字,圈出来,继续读下去。越读越觉得需要求证一下此唐晓峰是不是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位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学者。北岛在书中提及他是49年生人,我搜唐晓峰老师,48年,那同学一说应是说的通的。
后来又在网络上搜到两篇唐晓峰的文章,一篇是2011年登在《读书》杂志上,为北岛《城门开》写的书评;另一篇是2008年登在《书城》杂志上,题名<难忘的一九七一>,也收入了北岛、李陀编的《七十年代》之中(这本书的编写缘起也与唐晓峰有关,见后文)。
从这两篇文章知道唐晓峰与北岛是四中同学,北岛低一级。唐晓峰与刘羽是邻居与发小,而正是通过唐晓峰介绍的刘羽,北岛认识了芒克等人。唐晓峰曾尝试写诗,本来打算给《今天》投稿,可惜后来被北岛浇了冷水就不再写了。若干年后,唐晓峰再写北岛《城门开》书评,颇有专业色彩,值得一读。
自以为挖到了八卦,兴奋地告诉很欣赏唐晓峰的学长,反被推荐了北岛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三联书店,2012),其中也收录了唐晓峰的一篇文章<走在大潮边上>。其中介绍唐晓峰是“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
(注:下文有大段对原文的引用)
先说<难忘的一九七一>一文,有几个片段提及北岛: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相似的内容,在<走在大潮边上>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难忘的一九七一>中还提到:
“……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著的人。)
“一九七一年年底 ,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也是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经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据,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一九六九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
后文中还有唐晓峰老师与北岛聊诗的旧事:
“一九七一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做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应该是拿回来了),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朦胧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得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接着,唐晓峰也谈了他自己学写诗的过程(我个人由于猎奇心态很感兴趣):
“某一个兴奋的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的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乎得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
二〇〇七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之后,唐晓峰写到自己的邻居、发小刘羽,他应是北岛<波兰来客>一文中提及的老刘: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二〇〇三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在<走在大潮边上>一文中,唐晓峰在开篇就提到邻居刘羽:“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院里的刘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在十三中。”
唐晓峰在<难忘的一九七一>这篇文章中还是显露出地理学情怀,比如对经常举办聚会的刘羽小屋的感叹:“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一九七一年,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一九七一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得曲子是《黄河》……”
(其实看到文末我才意识到以前看过这篇文章。)
另外,说起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一书的缘起,李零在2010年2月《读书》杂志上<小人物与大事变——关于《七十年代》的讲话>中提及:
“这个集子是北岛、李陀编的,我只是作者之一。
‘七十年代’很重要,对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很多人,很多事,都值得重新回味。
过去,我跟唐晓峰谈过这事。他跟北岛是老同学、老朋友。北岛移居香港后,他跟北岛说这事,北岛一听就说好。他是个说干就干挺能张罗的人,居然约了不少人。他和李陀编这书,出得真快,二○○八年出“牛津版”,二○○九年出“三联版”。原来只是说说,想不到这么快,书已经印出来了,一下就有了两个版本,香港和内地都能看到。”
再说唐晓峰在2011年1月刊载在《读书》杂志上的<北京的存在——读北岛《城门开》>一文,带有其个人专业视角。恰巧,我最开始接触北岛差不多就是《城门开》一书。
唐晓峰提及于他与北岛来说都比较重要的地点,这些地点于我也很重要:
“六十年代后期,我们进入高中,开始领教同类间的厮杀,于是我们告别童真,进入‘文明’了。我们开始在‘革命’道路上前进,学习同类相残。‘文革’中,京城、校园成为同类斗争的战场。走向斗争,是那一段人生的‘大方向’。现在做反向回忆,我愿意跳过‘文明’期,归依五十年代。北岛谈到什刹海地区,这是现在京城所剩留的不多的‘老区’。北到德胜门一带,南到平安大道,东起鼓楼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这就是什刹海地区的范围。今天有一个‘什刹海文化研究会’,专门研究这一带的历史、文化。什刹海地区的几个关键地方北岛都说到了:护国寺小吃店、后海积水潭、德胜门、护城河、百花深处(一条小胡同的名字,民国间曾用作有轨电车站名)、烟袋斜街,等等。从这个地区过来的人,一辈子都揣着这些地方的故事。对我来说,只要护国寺小吃店还在,我的童年就没有远去。”
他们混迹的地域也是我在这里混迹的地域,前几日中秋,吃到了护国寺小吃店的翻毛月饼,甚至有种可以把北京当做故乡的感觉。
唐晓峰还谈论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关系。“时间不易察觉,而地方场景的改变会告诉你时间的运行。守护场景,可以守住时间(我学的是历史地理,也可以反过来,作地理历史,用地理证明历史)。”
同时,唐老师不忘自己“文化地理”的本行,提及段师傅:“童年的感受非常重要,有的人一生都履行在童年确立的朝向中。美国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总爱回忆童年的地方感受,他写的《恋地情结》,是美国地理研究生的必读书。”
当然,“地理学史”也是唐老师的兴趣方向:“ 一切都是可能的。一部地理学史可称作《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杰弗里 ·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八年版),北京城也是座All Possible城市,里面有帝王世纪,也有草根故事,有成人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有各色少年之烦恼。是哪个范畴在催生、培育真正的北京史家?我们这一代人,在这座城里,做过‘祖国的花朵’、‘雷锋式的好少年’、红卫兵(造反派)小将、老三届‘插青’等,其后再无整体命运。但无论各人的运势怎样,内心都在守望这座城市。”
在与旧事发生几乎相似的地点,看到唐晓峰写的相关回忆文章与其对个人体验下的“时间与空间”概念的表达,感到分外亲切。
另外,北岛本人在查建英主持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自己的被访谈部分提及唐晓峰:
“查建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与‘白洋淀’那一圈朋友认识的?请描述一下当时交往的方式、人、话题,等等。
北岛:我是一九七二年冬天通过刘羽认识芒克的。刘羽是一个工厂的钳工,‘文化革命’中因‘反动言论’入狱三年。我又是通过我的中学同学唐晓峰(现在是北大历史地理学教授)认识的刘羽。按唐晓峰的说法,刘羽是北京‘先锋派’的‘联络副官’。所谓‘先锋派’,其实就芒克和彭刚(一个地下画家)两个人组成的。他们自封‘先锋派’,然后扒火车到武汉等地周游了一圈,最后身无分文,被遣送了回来。后来又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芒克在白洋淀插队,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去看过他,以后和彭刚等人又去过好几趟。白洋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乡风情,吸引了一些当时脱离插队“主流”的异端人物,除了诗人芒克、多多(栗世征)和根子(岳重)以外,还包括地下思想家赵京兴(因写哲学随笔蹲了三年大牢)和他的女朋友陶洛诵,以及周舵等人。”
到这里,有关唐晓峰和北岛之间关系的“八卦”已经差不多了。想起前几日,有人以“空间与历史”为题做活动,还提及唐晓峰大概是最适合讨论这个主题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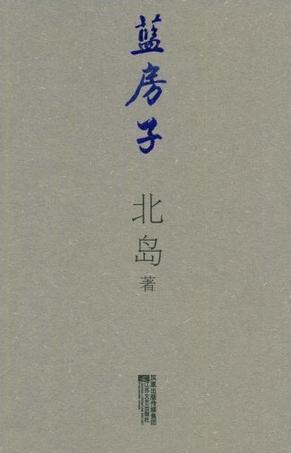
脑残粉……掘火是故意不做搜索的么?
有搜索框,在文章栏和博客栏之间